《永远的托词》剧情介绍
衣笠幸夫(本木雅弘 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和妻子夏子(深津绘里 饰)结婚多年,感情早已经由最初的炙热走向了平淡。尽管夏子一直以自己的温柔和坦诚包容着幸夫,但幸夫不仅不为所动,甚至以冷漠和粗暴回应,只因为幸夫的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福永(黑木华 饰)。 某日,夏子和 好友(堀内敬子 饰)结伴出游,哪知道乘坐的大巴半路上遭遇了车祸,两人不幸遇难。得知了妻子死去的消息,幸夫虽然内心里没有一丝波动,却还是在表面上装作悲痛的模样。之后,幸夫的生活陷入了混乱之中,负责他的编辑唾弃他,福永也离开了他,直到有一天,夏子好友的丈夫找到了幸夫,拜托他帮忙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在此过程中,幸夫渐渐学会了正视自己的软弱和不堪,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美国派(番外篇)4:集体露营第十三个夏天废弃公园阿伊努之森谜案追凶第二季最后的跳水青春王室第三季1947独立任务擂台女王恐龙鳄鱼大冬瓜女神.Angela执笔蝙蝠女侠第一季绝望主妇第八季格式化少女二捕出山爱情游戏无法恋爱的夫君路的尽头网飞喜剧会卧底公主泰坦第一季小房东西非历险无限生机当你年少时回复术士的重来人生爱情开始的地方之遇见斯托克
《永远的托词》长篇影评
1 ) 横亘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暧昧矛盾
作为是枝裕和的嫡传弟子,西川美和不仅从风格上一手继承其师细腻风格,在题材方面也是无限接近,比如今年师徒俩心有灵犀地将男主角定位于“作家”,只不过师傅聚焦于失意落魄的作家,而徒弟则将镜头对准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
有趣的是,两位作家在自己笔下的文本真实与当下眼前的现时真实都不约而同地陷入迷失。
《比海更深》和《永远的托词》两部影片均获得第29届日刊体育电影大奖四项提名,西川美和这部根据自己直木奖候选小说所改编而成的电影,亦得到是枝企画协助,更烙上浓浓是枝裕和的痕迹。
序幕卡司映现时,深津绘里的名字出现得挺晚,心里还奇怪这么一位大牌怎么卡司位排得那么后面,毕竟这次她与本木雅弘的合作,是继1995年《最高的单恋》之后时隔21年的再度共演,加上本木雅弘也是继《入殓师》后,暌违七年后重返大银幕,相当令人期待。
剧情推进一刻钟后,心里大约有数了,如同西川美和酷爱的以死亡、葬礼、失踪或意外为正片引子一样,此番又是将死亡阴影先行笼罩全片。
从处女作《蛇草莓》爷爷的葬礼开始,西川美和的惯用手法就是以死亡为分界点,倒叙回忆,贯通未来;《摇摆》以真木阳子不明真相的失足摔下吊桥,引发兄弟间看似牢固的情谊摇晃震荡;《亲爱的医生》则以笑福亭鹤瓶饰演的庸医伊野治失踪为悬疑倒置,众人记忆闪回拼凑出的往事拼图;《卖梦的两人》稍有变奏,不过也是一出异于日常的变故——一场将家产烧为乌有的大火,铺展开故事。
深津绘里在平静甚至颇为冷淡地帮作家丈夫津村启剪完发后,就与闺蜜出发旅游了,关于她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摄影机慢慢贴近她的视线,变为主观镜头,望向白茫茫的车窗外,从深津绘里冷而麻木的眼神里,观众很容易被移情,为下文的悲剧有了一点点心理铺垫,甚至我会得出这样一个类似幻想的结论:夏子是否预感到了悲剧?
镜头切到正在偷情的丈夫那边,在凸显衣笠幸夫的行为于性格的目的功能上,能轻而易举达成,但这种大反差的偷懒方法和后面流于说教的桥段一样,往往不能满足观众深层次的情感需求,也让某些资深影迷对套路化的发展失去期待,可能这是西川美和与其师的差异所在。
不过是枝裕和近年来也越来越温情化,越来越四平八稳,大波动大幅度的情节走向渐渐少了,《永远的托词》剧本反而有是枝裕和早中期的影子。
从拒绝夏子当众唤他“幸夫”开始,我们心里大约对这个人有了初步定位——虚荣自大,自以为是,无视妻子,忽略过往,功利性强。
因此当出轨对象也讨厌起他时,性格的树立及发展已经完成大半,衣笠幸夫被年轻女孩指责“谁都不爱”时,茫然及麻木的神情十分到位,他其实就是一个躲在壳里的可悲自大狂,沉湎于光荣历史的人气作家,已然走上下坡路,编辑诘问他的话令他恼羞成怒,不过他依然十分享受扮演一个“沉浸于失妻之痛”的名人,葬礼上得体的致辞和诚恳的悲伤表情,内心不由对自己万分满意,竟忍不住在网上搜索起评价来。
这些虚张声势,到底也抵不过内心发虚,搜索词的逐渐变化体现了幸夫色厉内荏的本质,人物形象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些细节铺设都是典型的西川美和风格。
与其完美公众形象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夏子闺蜜的丈夫——大宫,一个大大咧咧、动辄痛哭的粗鲁男人,性格简单直爽,感情充沛浓烈,阳一代表着衣笠幸夫不远回首的平淡过去,因此幸夫一度拒绝阳一的存在以及单方面闯入其生活的意愿。
不过,当幸夫目睹阳一一家乱糟糟的生活时,或许是出于心底残存的一丝温柔,或许是怀着找寻素材的目的,也或许是想打破目前固步自封的状态,更或许是全因连他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某种优越感(两处住所的对比),他开始进入大宫阳一和两个孩子的生活。
西川美和在拍摄《摇摆》时曾表示:“兄弟,这仅仅是靠血缘,被连结在一起的两个人的关系,是多么的稀薄和危险。
这就是我想要描写的。
当然,这种关系也有发展的可能性。
我个人的希望,是通过这部影片,能够发现人和人之间心的相连。
”这番关于接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宣言可视作她所有作品的宗旨,也是她所有作品的素材灵感源泉。
幸夫与男孩真平与女孩小灯之间的关系从不无对立到慢慢融合,通过几组有意思的镜头表现——深夜等候公交车、看动画片、吃饭、骑车上坡等。
这个阶段的幸夫在外部行为上似乎有所改观,甚至在和大宫阳一一家去海滩时,幻觉中出现夏子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故意误导观众,仿佛幸夫内心的冰山有所融化,影片基调往“治愈”方向越靠越近,可是观众心里仍有疙瘩,毕竟幸夫至此一滴泪都未流过,即使他已不再爱妻子,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非正常的举动。
这个奇怪的细节被两个人捕捉到——一个是夏子生前的理发店同事,质问幸夫“你想过她的生活吗”;另一个是幸夫的助手,池松壮亮的戏份不多,但对剧情有助推力,他不动声色地问幸夫:“老师你还没哭过吧?
”。
幸夫当然很尴尬,是的,尴尬混合着麻木,以“套中人”的乐观无畏扮演着保姆的新角色,并享受着与“失妻名作家”同样本质的虚荣角色。
如果这么拍下去,影片很快就要滑向平庸的深渊。
西川美和抛出了戏剧转折,首先是破坏幸夫和大宫阳一一家以及小灯的老师共处的和睦氛围,西川美和再度运用其剥离生活真相的拿手好戏,在剥掉第一层“功成名就,岁月静好”的皮之后,继续剥第二层“互助即救赎” 的皮,这大概就是平庸导演与好导演之间的区别吧。
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不提伤心往事、无视伤疤并未痊愈,而变得温馨美好,心病依然是心病,梗结依然是梗结,小灯生日会上无心的几句话,揭露了每个人其实仍停留在原地,问题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
其次是破坏大宫阳一与真平之间貌似相互谅解的父子关系(之前几乎未正面提到),父亲独自沉浸在失去妻子的悲痛之中,却未意识到孩子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折射了妻子还活着时,他作为父亲缺席的事实。
再次是继续破坏观众从影片第一幕获得的观感,幸夫从夏子手机里找到了最后一条未发出的信息:“我再也不爱你了,一点也不。
”他的壳终于全碎了,所有的假装和扮演像是一出丑陋的滑稽戏,他照见了自己的丑陋和自私,他的无奈和绝望,他的无能和冷酷,以为站在世界巅峰,其实早已跌落谷底;以为可以装作和死亡共生,其实早已行尸走肉;以为人生很长,其实往往来不及告别,而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和死亡较量,已经无法说声“对不起”,这也是他终于撕碎温情面具的决心临界点,也就是他和大宫一家暂时断交的契机。
幸夫也终于发现关乎妻子的记忆不仅单薄,而且充满疑窦,关于记忆的自我篡改及不确定性这一特质也是西川美和在历年作品中反复呈现的,如《蛇草莓》中哥哥十分确定找到的蛇草莓,妹妹却从未找到过,如《摇摆》中弟弟对哥哥是否故意杀人的判定,如《亲爱的医生》中村民回溯医生从医经历。
你所看到的生活远非生活,你所听说的人生远非人生,记忆会说谎,记忆会欺骗,记忆交织着秘密与谎言,谎言与真实之间存在着暧昧的矛盾。
幸夫在回忆的迷宫里再次丧失生活的动力(如果说之前担任保姆,让他至少在表象上拥有“治愈”的可能。
),重新堕入毫无意义的生活。
这三个破坏是整部影片的转折点,并逐渐引发影片的高潮,让分崩离析的人物角色们再一次聚拢,彰显剧本的扎实与打磨功夫。
大宫阳一由于和儿子争吵心烦意乱,开卡车出了车祸,剧情并未滑向进一步狗血,克制止步于轻伤,重点给到幸夫重新联络上真平,两人一起赶往车祸当地医院,一路上一大一小心结的逐渐解开,让影片的情感逐渐趋于高潮,而阳一和真平的相互谅解,让独自乘新干线回来的幸夫遁入光明,灵感突降,久违的文字重新落于笔端,他写道:“人生,就是他人。
”我得承认,这句话非常说教,非常心灵鸡汤。
可是我也要承认,真的被结结实实感到了。
失去亲人的悲痛容易理解,但如果是一个将自己隔阂于心灵之外、放逐自己于人伦之外的局外人,他的悲伤,可能要等许久许久才能软化、稀释成触手可及的温度,这种老生常谈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救赎」。
那些曾放弃生活的人们,终于在历经误解与释然、落魄与奋起后,拐入意料之外,珍视生的每一刻与死的另一边。
影片的结尾,你尽可以贬之为可预测的鸡汤套路,但又有什么关系?
纯净如冬日阳光的手嶌葵版《绿树成荫》,像远处春日汩汩流淌的山泉,将身心涤荡一清。
以剪发开场,以剪发收尾,结构合拢,时光走了一圈,即使物是人非,即使谎言与真实继续暧昧继续矛盾,即使我们只能做远望的平行线,我们依然相爱。
2 ) 逝者赏味期
在后面剧情趋于平淡化之后,可看可玩味的地方可能就没有之前铺设的那么多了。
我一度认为自我意识强烈敏感思想复杂的人,在猛然经受了丧妻丧偶这样打击时,其对这种打击的反应速度是没有那些心思单纯表达感情方式直接的人来得快的,具体参照作家和大宫,作家和真平,真平和大宫。
在这三组人物关系之中,作家在得知自己妻子死去之后,从认领遗物到举办追悼仪式,在这个过程中,都处于一个茫然的状态中。
不知道妻子出走时穿的衣服,也不知道和妻子结伴出行的人,妻子离家后也不曾与自己联系,到采访结束后进入车内时观察自己的发型,开完追悼会后上网检索有关自己新闻,生怕自己不伦的这个一事实会由妻子逝去为出发点引爆。
男主在这个阶段中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可以看作是夫妻关系冷漠的佐证也可以说是男主自私人格的表露,到作为电影的一个序列而言,这个过程其实是男主进行摸索性确认的一个过程,即曾经一直活在自己世界里离自己那么近的妻子真的就此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吗?
这种接受亲人逝去的体验由男主善于观察的眼睛记录了下来,作为事故责任方的反应,作为妻子朋友的反应,作为媒体的反应,作为其他遇难者亲人的反应,其中在遇难者亲人的反应最为重要,面对自己亲人的逝去,到底怎样的反应才是正常的呢?
大宫的反应是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且通过一直播放妻子最后的语音信息来怀念妻子,对外界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悲痛。
儿子真平的反应是十分冷静,因为“没有哭”就被认为不爱自己的母亲。
从这点来看,真平的性情似与作家相像,敏感细腻而不将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随意向外表露。
但从反应程度而言,作家和真平这类人与大宫这类人相比,其对亲人突然逝去的这一反应程度是更为深刻的。
因为他们会通过之后亲人永远的缺席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来逐步确知亲人逝去的这个事实,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许多困扰他们一段时期的情绪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可能就是赎罪心理,而对真平来说,可能就是对之后这个家庭走向的担心。
所以到了影片后半程,两端矛盾冲突得以突出,即作家教导大宫忘却,大宫真的忘却了作家自己却不愿意忘却的矛盾和大宫忘却后对家庭的疏于照顾以及真平在母亲去世后强制自己自觉执行的照顾家庭的义务的矛盾,这个矛盾大宫疲劳驾车受伤这个事件的发生才得以解决,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作家顿悟比起活在追忆逝者的痛苦中,仿佛把握住活在当下的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使得真平忏悔自己曾希望爸爸代替妈妈死去的罪恶心理,意识到爸爸在自己的世界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在主题方面,编导似乎更侧重于人在面临打击之后的相互自愈,而止步于婚姻中出轨一方在妻子去世后的自我问责。
中间时段穿插的电视访谈节目拍摄,也似只是在唤起丈夫在妻子逝去的孤独感与对妻子的想念,或转向另一方在表明个人的死亡不能使整个社会停止运转这样的宏大主题,戏谑式的镜头语言也不意在表现人情的冷漠。
毕竟,死亡始终也是件关乎个人的事,愈疗也需和有相同经历的人一起进行。
3 ) 《漫長的藉口》觀後感
妻子要趕去車站會合摯友結伴旅遊, 她在出門前還是惦記丈夫那把稍長的髮絲, 丈夫是小說作家, 他不時會於電視節目接受訪問, 丈夫髮梢長短不一或朝天翹起是身為髮型師妻子不能容忍的, 髮理完, 妻子說了一句完美拉了旅行箱出門。
妻子眼中完美的丈夫是倚著合時髮型勾搭情婦的混蛋。
徒生劇變, 妻子同好友同葬冰河, 作家於妻子喪禮致詞時感慨的說理好髮根殘留了妻子纖指的溫度, 幸夫於家屬親友當前神情憂傷, 他捧住妻子骨灰盒步出靈堂有攝影機捕捉名人舉動, 作家低頭哀傷的帶亡妻灰燼登上轎車, 這刻鏡頭拍不了脫了假臉具於車內後照鏡梳理前額頭髮的作家, 妻子的體溫早已散去, 他仍然要活下去, 他指頭觸感實在, 他未能於妻子事故下淚, 幸夫夏子畢竟是相處二十年的老夫老妻了, 妻子身體髮膚已是倦透, 夫婦話題能說的都說了。
幸夫於十九歲於理髮店邂逅髮型師夏子, 少女理少年的髮, 她的手指撫慰了客人頭皮, 首截肌肉輕按力道張開了來客的作家夢, 丈夫的事業有成是他初結識美女時她鼓勵有志者不倦的執筆, 所以作家刻意留長頭髮記念今日的盛名, 就是日後錄影電視節目工作人員安排好的理髮師作家婉拒了, 髮根是丈夫與亡妻的感情聯繫, 亦是夫婦定下來的談天說地, 丈夫對妻子的懷念藉著長及肩膀的曲髮留住了, 淚水早已滲入血管供養妻子不會再打理的亂髮。
幸夫喪妻後家裡凌亂, 情婦按鈴探訪, 老師壓抑的慾望要爆發, 他穿了衣服強行與女人交合, 她同樣的衣衫整齊, 她抱怨男人不是那個於髮膚交纏前喝紅酒, 播黑膠唱片的優雅男人, 而是不知做愛為何物的糟蹋男人, 女子還未在男子完事前退出, 男子不知所措失去唯一的錯愛, 女人不留情面的不讓她愛過的老師洩射是她了解幸夫是不解溫柔的自私男人。
夏子在世時丈夫視女人為打理家務的賢內助, 以及保證出鏡儀表堂堂的造型顧問, 夫婦情是逝去的流水作業, 作家於令他妻子身亡的肇禍公司出席聆聽會, 對方負責人藉詞車禍司機執勤記錄良好, 難以理解意外原因, 數下響聲打斷了發言人解釋, 貨車司機大宮陽一拋擲的雞蛋染黃了似是無辜事端的交通機構, 陽一大哮的[把我的妻子還來!]有如炮彈轟破在座遺親危危欲塌的維繫家屬思愛城牆, 他們大聲叫罵胡亂推塞的發言人, 場面一度失控, 唯獨那個默默聆聽, 表情苦悶目睹叫囂不助拳的大作家扭曲嘴巴離座, 幸夫到來不是追討責任, 而是在世人, 特別是愛戴他的讀者面前做好公關門面工夫。
多年沒有兒女的幸夫提出一周幫忙陽一看家帶孩子的義務, 作家初時強調他只要手提電腦在手, 何時何地可以寫作, 幸夫的說法一來是去除陽一膽心他上門看顧孩子會打擾作家的寫作日程, 二來是作家沒有靈感下墨, 他急於要在新鮮事物開竅, 帶孩子上課、煮食及開解長子真平及同小女孩灯看動畫是他先前沒有的人生體驗, 幸夫於陽一抱著女兒回家碰面的剎那收起了筆錄真平睡覺模樣的筆記本是作家利用人性軟弱突破撰文困局的私心。
與女孩常處日久, 幸夫渾忘寫作, 男人把男孩女孩當做一家人, 男人騎腳踏車載女孩沿斜坡歸家, 他力氣不繼的差點摔倒, 女娃兒笑他比不上一口氣載女兒回家的媽媽, 男人聽了更是不服輸的用力踏著足板拉動齒輪, 他明白女孩會長大, 他有一天總會離去, 他要在還能照料孩子的日數用心用力, 這不是作家找尋創作泉源, 而是代父體會不會有兒女, 他把為父心願短暫寄託, 亦是把妻子沒有子女的命數, 連同丈夫的份至大宮家陽一要父替母職的不全家庭。
不生兒育女幸夫嘗了保母滋味, 他的幫忙正好填補了陽一日夜顛倒不日在家照顧子女的輪休工作。
陽一的貨車司機行業是難為慈父難為親的苦差, 補習社不時致電兒子要他不要經常缺課, 主任問學生是否周日回校測驗? 學生答應, 他能否定時上課他不能肯定, 他要照顧妹妹, 他要告訴爸爸情況時父親抱頭大睡, 母親早逝, 父親是一周數天不在家, 回家交錢予兒子添衣購食的不問家事, 無暇關心子女需要的長期疲勞; 那個缺乏二氧化碳化學常識及不管兒子是否順利升學的無求父親讓兒子十分討厭, 爸爸永遠不能代替臨出門旅行留下電話留言交帶丈夫要子女刷牙才睡, 以及要替女兒帶上尿片對家人無微不至的媽媽。
然而, 兒子從弄妹妹伙食, 接妹妹放學體諒父親工餘要照顧家人的辛勞, 也明白他身為男子漢要承擔一切的重擔, 怪父的心轉為讀書動力, 終能升學。
失去了的不可挽回, 兒子真平在世要補償母親不在的完好家庭, 幫助他輕看卻愛他甚深的父親。
幸夫剪掉了的亂髮是他終能釋懷不愛他妻子的悵然, 他勇敢發表新書是記述他的大變, 從沒有的愛有了家庭的愛; 陽一的刪除短訊是他能放下對愛妻的淚流憶起, 父兼母職, 與兒女面對人生起伏。
本木雅弘不是那些人到中年怕年華逝去刻意節食健身保持瘦削的偶像明星, 他是因應角色定了身型的務實演員, 他演的幸夫是養尊處優作家, 人到中年該有的小肚子他有, 他於影片露了的肉塊是好演員忠於演藝事業, 不是演什麼角色都要的裝酷耍帥。
Patrick Chan 寫於2017年1月2日。
4 ) 现实就是各种托词
看完《永远的托词》,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幸夫真的从妻子的死和大宫一家人那里学到了珍惜吗?
也许是有的吧,就像他在火车上对大宫儿子说的那样:“不要推开给你爱的人。
”但我觉得这忏悔终究是要落空的。
即便幸夫重新写作并获得成功,这种成功也让人质疑。
或许电影把写作理解得浅了吧,写作是为了赎罪,但首先是为了要面对罪。
幸夫始终在逃避,在表演,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舞台安放自己的良心,但这个舞台事实上是没有的,就连亡妻都没有给他,大宫一家也同样。
电影海报是小夏和小雪一家在一起。
但事实上这只是幸夫的幻想,现实中小灯送的照片里只有小夏一人。
我觉得现实是拒绝幸夫忏悔的,不会给他机会救赎自己的内心,或者说现实就是各种托词,由各种行得通的理由组成。
真正的忏悔和救赎必是背着向现实的,是向神的行为。
5 ) 完整也雕琢,感性的回归不够感性
从异性视角再体验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隐忍付出的影片不算少,这部在其中谈不上多好,影片自幸夫对妻子夏子出门前神经质的表现(还不让夏子使用一直以来喊着的“幸夫”的昵称)、夏子在巴士事故中猝然而逝开始,从夏子密友的丈夫阳一热情接触男主幸夫正式展开,阳一是真性情到在发布会上痛骂事故方的男人,因妻子关系而对温和友好的夏子及作家幸夫夫妇感兴趣,此次两人同时沦为事故的受害者,他抱以互相疗愈的态度给幸夫的电话留言。
幸夫正因为自己在事发同时间的偷情而失魂落魄,并且几年间的创作表现也趋于平庸,或许被对方这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态度触动,或许想寻求写作素材,他应下了会面的邀请。
第一次见面就出了事故:身边无人照料小孩,阳一带上了自己的儿女一同去餐厅,而因为妻子在世时他很少带孩子,使得女儿灯吃下了餐厅含有螃蟹成分的前菜过敏,阳一慌乱地带上灯去了医院,并托幸夫暂时看照儿子真平。
与真平独处的经历中,他了解到由于没人带孩子,真平已经(在小升初阶段)休学了,而他对于学习的态度明明很认真努力,他表示愿意每周到阳一家里照顾孩子,并接送真平上下学。
幸夫也没有带孩子或是照顾他人的经验,因此一开始手忙脚乱,也对兄妹俩的打闹无从下手,但即使如此,还是与孩子们打好了关系。
受到信赖后开始变得温馨顺利起来,直到在参加回忆亡妻的电视节目之前看到了妻子手机上给自己未发送的短信“我不爱你了,丝毫不爱”。
随后是尴尬、虚伪的拍摄过程,在阳一家庭中所建立的某种真挚羁绊,间接的对妻子的感情,突然间又破裂了,回到了一开始的状态。
一开始在妻子的事故报告会上,幸夫也是一心关注着自己形象、媒体报道,还想要跟情人温存逃避现实(因为太不当人情人也跑路了),与阳一暴怒的表现截然不同。
一次灯的公开课上,实验结束后,老师优子提问阳一自己和灯向瓶子里吹出的气体中包含什么成分,没想到给出提示后也没能令这名大巴车司机回答出“二氧化碳”,造成尴尬。
正当幸夫对阳一说,明年自己有可能不能再带孩子后,优子走过来向幸夫表达了自己的敬仰、对亲人离世的共情,这激起了幸夫的不满,当下离座。
又一次,在灯的生日上,优子表示自己父母有在做托儿义工,幸夫表示不信任,在阳一一家人团聚的饭桌上大谈带孩子的不便,矛盾得到激化,幸夫没再去阳一家。
真平本来就牺牲了自己的很多时间在照顾妹妹,又有升学压力,并且从一开始灯过敏时的场景里就有表明真平比阳一更体贴灯,阳一对两个孩子的关怀不够,真平觉得自己的父亲很不争气。
一天深夜,真平在补习的过程中打游戏吵醒了阳一,阳一说不管玩游戏还是学习,身体都是第一位的,并引申自己的工作时都会先补眠再开车,真平则说学习跟开车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要混为一谈。
这激怒阳一,打了真平。
随后,阳一在工作时车祸入院。
另一边,幸夫则在纸醉金迷中痛苦。
幸夫听闻阳一入院的消息后赶紧跑去了阳一家照顾孩子,随后,在归途的火车上幸夫开始重新写作,写出了电影的同名作《永远的托词》。
写作大获成功,幸夫去了妻子生前工作的美容院理发,葬礼上向幸夫大发脾气的妻子好友欣慰地为他理发。
庆祝夺得文学赏的发布会上,阳一一家出席,真平跟灯发表祝贺感言。
作为幸夫而在阳一的家庭结成羁绊,得到文学感悟(素材)的主角,仿佛得到了亲密关系与文学创作的双重救赎。
全片对于夫妻关系的刻画基本还停留于男性对女性的情感依赖、生活需要上,并且由于两个小孩对幸夫接受得很快,使得观感上反而是男性轻易填充了原先妻子存在的空间。
后续产生的问题也是在两个男人发生矛盾,出现不一致之后,而这在异性关系中也是大概率会影响到孩子的……更何况,哪怕是这种级别的缺失,还是在阳一的家庭中拟态发生的,男主在失去妻子后暴露的那种空心化,跟夏子真的有很大关系吗?
一个无心无德的人因为认知上重要的人猝然离世而受迫拷问自己一直以来的忽视,更像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了,但假如这不是两对夫妻间的关系,而仅仅是一个单身汉与一个家庭的关系,那么在阳一家所发生的种种就变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温情的替代品罢了。
尽管这也是一种“托词”,但份量上是截然不同的。
开头对幸夫那惹人不满的神经质表现,也几乎在第一幕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男主在正常人限度、甚至显得过于热心肠的容忍,以及对于过往只剩下了温情的讲述,使开头那一幕变得孤立了起来。
尽管可以说这是在妻子离世、情人离去之后的清醒,但类似于这种“即时影响”的剧情表现在剧作上不断重复,导致人物为了情节上的起伏而割裂,显得反复无常。
情人跟妻子在美容院的同事朋友、名为优子的教师也是这种扁平创作的表现之一,明明情人一开始还显得对夏子颇为嘲笑、对立,在夏子出事后态度却立马迎来了拐弯,而同事也是在开头的怒骂之后就只剩下了结尾的欣慰表现,这两个人都只有完全的工具属性,用来衬托幸夫的空心化或是自我救赎;优子则所有戏份都在造成尴尬,对幸夫施压(不是有意的),迫使剧情短暂地走向负面。
一切都丧失了本应有的复杂性,显得单调呆板。
更别提幸夫在节目录制前看到妻子的“分手短信”、阳一在幸夫说“该忘掉过去了”后删除妻子的短信、阳一在真平爆发后立刻遭遇车祸……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有时戏剧化创作就是巧合的集合,但如果这是一部有严肃表达的作品、所有表达所需要的转折却都由唐突发生的意外来提供,或许我们不得不质疑这样一个故事的可靠性,以及人物在适应意外后所得到的收获,究竟与先前的家庭关系有多大联系。
作为故事主体的幸夫也始终披着一层迷蒙的外衣,电影没能很好地向观众展现他的心理历程。
此外,我个人很不喜欢在电影后期反复出现的突出幸夫纤细感(感性)的镜头,很媚俗。
幸夫跟助理交谈家庭关系,提到“照顾孩子”就像是男人的赎罪劵这一幕尽管也可以说是刻意营造的尴尬氛围,但还是有稍显生硬的说教气息。
另一方面,影片前半对幸夫照顾两个孩子的呈现还算可圈可点,两个孩子既有孩子气的一面、也有听话机灵的一面,并且体现孩子对幸夫接纳的转折也不像后续阳一车祸那样一板一眼,一定程度上令人意外——沉默寡言的灯主动解围,为什么叫叔叔,因为你和爸爸太不像了。
真平对灯的照顾,灯造成的麻烦,累到哭泣的真平……素材的生活气息还算不错。
恋爱时妻子对自己的昵称被阳一的家庭所继承,唤醒了数年间没能创作出好作品的作家,的确是一种感性的回归。
6 ) 忠于感受,保持怀疑
七月不巧只买到这一张票,但它已经满足了我的七月小西天之旅。
第一次在电影的转场镜头里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角色的情绪流动和心境变化,而不仅仅是对下一幕的切换或衔接。
好几处细节的捕捉都精准还原了生活与人性,浏览器搜索框里名字后缀的变换巧妙地将幸夫的情绪从自大过渡到自省。
幸夫接到阳一车祸消息一幕通过一个窗户的远景将观众的视线聚焦于幸夫慌乱的反应,这个镜头设计相当精妙,同时完成了电影里最大的对比,流露出幸夫对夏子车祸过度冷漠的愧疚。
当我和幸夫一样确信夏子已经不爱他了,映后导演一语将我点醒:短信草稿箱里留下的文字也不一定就是夏子的真实想法,也许她当时只是在气头上。
虽然文字往往是真挚、私密的,但依然存在虚假的可能性,有时我们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
刚开始对于幸夫这样集缺点于一身的男人非常反感,对他能展开什么故事并不感兴趣,但好在影院的座椅能把我的身体连同耐心一并锁住,我才能完整地感受这场电影。
剧本也并没有着力打击幸夫的事业或感情,只是通过参与另一种质朴喧闹的生活让幸夫摘下一层层虚伪的面具。
要说电影的不足就是幸夫的转变确实有些突然,导演解释这是幸夫急于依附正向的、彰显责任感的事情来抵消他的罪恶感。
也许问题就在于电影里并没有表现出罪恶感的存在。
想多看些西川美和导演的电影。
希望日后能一直忠于自己的感受,落笔时不加虚假的粉饰。
7 ) 不要悬浮于生活
(文/杨时旸)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或者某种强大的外力迫使,他们会终其一生处于一种自我营造出的假象之中,并且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
那种假象像是一种惯性,维系着这些人的虚荣,也铸就着他们逃避现实的通道。
就如同《永远的托词》中的幸夫,作为一个三流小说家,已经多年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他变得势利又油滑,只依靠着曾经残留的名声,在电视台以嘉宾的身份插科打诨,卖弄小聪明为生。
他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和名气重于其他任何一切东西,终日周旋于温柔宽容的太太和年轻的秘密情人之间,自鸣得意。
妻子和闺蜜在外出旅行期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幸夫生活的惯性被彻底打破了,而这却让他意外发现了自我救赎的方向。
妻子的亡故,对于幸夫来说是一次难以名状的变化,或许,他都未曾料想到这件事会给自己的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在葬礼上,这个男人更在意如何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镜头,如何扮演出一副真诚又标准的鳏夫的悲痛样子,致悼词之后,他在车上,下意识地对着后视镜整理着发梢,导演安排出的这个举重若轻的小动作渗透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残忍,妻子尸骨未寒,他却更加在意自己在镜头中的妆发是否整齐。
从这个意义上说,幸夫一直处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里,他对妻子毫无感情,对情人也毫无感情,至于和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肉欲不如说是逃离,用一具鲜嫩的肉体和对方眼神里的无限崇拜,摆脱自己空洞内心中的可怕回响。
他一旦不纵情声色,不注重名声,就不得不与自己的内心对视,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的逼仄,他拼命打磨外表,重视虚名,不过是为了掩盖内里的腐烂。
当妻子闺蜜的丈夫大宫前来和幸夫打招呼的时候,幸夫不会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和眼前这个粗糙的男人会成为朋友。
但这个单身父亲和那个年幼懂事的孩子,却让幸夫一点点感受到内心的变化。
幸夫和大宫像一对尖锐的反义词。
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底层劳工,一个在妻子在世时就长久地欺骗对方,一个在对方过世后仍然念念不忘,一个像悉心打磨的瓷器,一个如同从未雕琢过的粗陶,他们的存在,彼此映射和对照,也彼此反讽和矫正。
大宫投入人间烟火的蒸腾,所有生活里的小确幸和小困境,他乐在其中也挣扎扑腾,而幸夫和真实生活的关系更像是磁悬浮,既无法投入生活丰沛的细部又无法真的超越一切琐碎。
换句话说,他的生活虚假又充满矫饰,与现实关系脆弱。
而他与大宫父子俩的交往,成为了他重新进入真实生活的过程。
最初是旁观者,后来是参与者,再之后,一点点变化,变成了大宫家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开始投入了感情,和孩子之间产生情谊,和男人之间也会争吵,这种争吵也是一种真实,相较于他当初在妻子尸骨未寒时整理发梢的自己相比,此时在路边发泄感情的幸夫更加可爱。
这个过程,更像是慢慢剥开了一颗外壳坚硬的竹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柔嫩的内核。
那些世俗声名、自负与矫情的包装都在真切的人间烟火熏蒸之下,一点点剥离殆尽,这犹如一次意外地提纯,一次代价昂贵地返璞归真,一场未曾预见的精神涤荡。
幸夫其实经受了两次外力的刺激,一次是发现亡妻手机中未曾来得及发出的短信,“我不爱你了,一点也不爱了”,那句话让他明白,看起来没有存在感的妻子对自己的一切其实洞若观火,第二次,则是大宫和儿子面对生活时的努力。
前者是刺痛,后者是治愈,这个过程让他得以重整旗鼓。
最后,幸夫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
书写和创作,在《永远的托词》中更像是一桩隐喻,它意味着心灵和现实的接通,意味着精神的灵敏度。
他曾经陷入虚妄和虚伪,犹如行尸走肉,创作就一度暂停,什么都写不出来,而如今,却变得文思泉涌。
与其说它重新获得了灵感,不如说他重新拥有了真实的生活。
8 ) 微小幸福
幸夫是个小说家,一本正经接受访问,装有幽默感的样子上番目,总之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假如我和他互加好友,他的朋友圈应该会有和演艺人的合照,在明星居酒屋的喝酒照片之类的,总之他的朋友圈生活应该会让我很羡慕。
而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妻子不爱,在妻子死的时候,还与学生在自家的床上做爱的渣男。
身为小说家的他,被编辑骂作品没感情,接受不了批评便动手打编辑。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作为小说家却写不出小说的自卑,而且一直说自己是没用的人,最糟糕的人类。
只能在妻子死后,靠妻子的死,按着台本拍节目。
以上的种种都将虚伪又无能的幸夫展露无疑。
越自卑的人,越脆弱,才会越放纵自己。
出轨、打人,是自卑;在妻子死后,流不出一滴泪,是脆弱,没有直面感情的勇气。
一旦对谁有了感情,生活往往不得由自己。
当他遇到两个丧失母亲,父亲又无力照顾的小孩时,他的情感在慢慢恢复。
只有在孩子面前,他才会觉得自己有用,“照顾孩子就像免罪符”,是赎罪,做点好事让自己内心不受折磨,帮助妻子好友的一家人让曾经冷漠的他感受到了一点生活的快乐。
幸夫终于写出了新的小说,编剧赞赏他,人们举着香槟为他庆祝。
幸夫也剪了头发,目光变得平静,日子好像恢复如初。
然而已经破碎的心不会严丝合缝地结合,已经失去的东西也难有机会再拥有。
幸夫终将为自己的放纵付出没人爱的一生。
也许,西川美和只是想告诉我们,“珍惜眼前的微小幸福。
如果失去那些珍惜你的人,即使获得众人追捧的名誉,也只剩孤独落寞的人生。
”
9 ) 别让懂得来得太晚
“你觉得你不会失去他们,但他们转瞬就离开了。
” 比较中规中矩的鸡汤题材。
导演风格有点像后期岩井俊二和中期是枝裕和的结合体。
光线质感完美,许多细节设置极其抓人,可以看出导演灵性所在。
电影主要由三条线铺开,幸夫的感情线,大宫的感情线,还有真平的成长线。
其中幸夫的感情线和真平的成长线其实是可以看作同一条,根源就在于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的方式是极其相似的。
直率到冷酷的情感思维,缺乏认同的自卑感,自欺欺人的倔强,这一切可以透过电影中无数巧设细节窥探出来。
可以这么说,幸夫其实就是长大了的真平。
至于大宫的感情线,更多的是作为对照辅助作用,与幸夫的感情线碰撞从而延伸出对遗忘的价值和回忆的可能的深入探讨。
然而,这部电影也有些不足的地方,男女主感情的前设铺垫不够,以及后半部分的剧情设置较为刻意,凿造之感有些重,还有大宫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较扁平。
但尽管如此,就凭这部电影对细节的把控和拍摄风格,7.6的豆瓣评分着实低了,7.9-8.2分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分。
10 ) 迟来的理解与永远的托词
日本致郁系电影的一贯风格,打光昏暗,色调偏黄。
开头的二人对话场景显得逼仄,而沉郁,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中,两人在关系中的强弱姿态一目了然。
那个你以为会是电影女主角的女人,却在故事还没开始讲的时候,在男人与学生的偷腥的呼吸声中被宣告死亡。
随后男主开始冷漠地对待一切,似乎是漠不关心;后来情绪急转,开始以照看亡妻旧友的孩子来自我救赎。
电影的音效做得极佳,在男主沉思写作时,配上动人的背景音乐,伴以浓重的齿音与呼吸声,显得情绪逼仄而迫近;庆祝新书出版的片段里,背景爵士乐欢腾,融入了double bass,非洲鼓、萨克斯等元素,而男主静坐,显出一副“热闹是他人的”的景象。
最终男主在内心,与自己与亡妻达到了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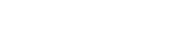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自我感动版早期是枝裕和。
導演改編自己小說,劇本很棒。小說應該很好看。但電影處理可以更好。像教小孩戲就比較弱。故事是一個...難聽點說渣男吧,從情感乾涸的狀態,繼而滿懷罪惡感,逃避,到自己都曾遺忘的情感復甦。要珍惜愛你的人,推開了,可能再也不會有了。本木雅弘好演! 深津演的妻子很美
人如何独自消化悲伤;少说别人,各有各的渣;成为父亲是男人的第二次成长;男主演技炸裂。
不是很懂这个回路
当逃避替代生活成为日常,依赖一旦戒断便是比逃避前更汹涌的无处可去。一树绿叶枯尽,主干才有冬阳下更洗练的笔挺。
同样是遇到重大事件后提出了人生问题 有些小感悟 却没有让我信服的答案
西川美和作为女性导演,表现男性丧妻的心理历程,如此视角的反转很有意思且具挑战(自我意识过剩虚荣虚伪的小说家如何在他者—两个小孩和憨厚司机父亲的介入下得以心灵净化,从而达到对妻子的赎罪和自我救赎)但说教煽情,深度欠缺,小孩表演调度差等缺点也暴露无疑(开头剪头发那段夫妻间的对话反倒是
补标2.5 有点忘了是哪个电影节看的,不功不过,对西川美和最早的印象应该是梦十夜,那个时候的西川在市川昆实相寺昭雄面前都没怯场
“因为死亡痛苦的,不是死去的人,而是留下来的人。”明明知道很多事无法改变,有时还自暴自弃,伤害周遭的人而毫不自知。人心如此脆弱,却又意外的坚强。去年的寄居蟹或许换了一片海,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抓紧那些珍视的人,绝不松手,付出更多的爱来纠正错误,弥补遗憾。
出电影院的时候想起了《幻之光》。
本木雅弘顶着油腻的发型渣老婆当奶爸都是为了衬托结尾的帅
以为人生很长,其实往往来不及告别,你无法和死亡较量;以为站在世界巅峰,其实早已跌落谷底;以为可以装作和死亡共生,其实早已行尸走肉;人生,就是他人,就是珍视生的每一刻与死的另一边;打开手机看到那条最后的信息,从剪发到剪发,时光走了一圈,我们物是人非。
人物很好,表现都不错,本以为想讲深邃一点的故事,慢慢沉下去,转折到照顾小孩子就俗了,鸡毛蒜皮,零零碎碎,本本雅弘的虚伪、自责、无力,缺少真正的灵魂支撑,后面又拉回来了一些。西川美和不愧是是枝裕和的徒弟,还是没彻底走出小清新的内核,拍着拍着,又回去了,甜腻,感性,不理智了。
这才是小说家的电影该有的模样啊
没有蛇草莓精巧,好丈夫和好爸爸其实是两种角色,婚姻强行把这两者合二为一了
A fresh slice of life
太中规中矩,情节推动却又有些突兀。貌似自然的不自然之作。
以为不会轻易失去的,崩毁只需要一瞬间。振作,或是重新出发,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呐。
多棒的题材没被拍出来,被老大是枝裕和一样风格的过家家耽误了半部片的时间,忘记了自己本应犀利的存在。
打开她的手机点开 短信草稿 写着 我已经不爱你了 丝毫不爱了 突然就是一阵扎心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