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剧情介绍
《阿拉姜色》长篇影评
1 ) 无标题
一直对女主的离开方式耿耿于怀,觉得电影编的还不够合理。
关于朝拜、皈依等,应该是一个忏悔和思过的过程。
痛苦到极致后对执着的忏悔,包括个人情感,每次的头触土地,换来的应该是解脱与轻松才对。
可能电影关注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吧。
123457788913345667889946543254378332
2 ) 伤痛是一个值,往往落在善良人身上 [猫]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18年11月某期。
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阿拉姜色》是在今年上海电影节获得广泛好评并抱回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奖的热点电影,即便排片不大,不密,依然在近期颇受关注,并获得挑剔的男性影评人群体的肯定。
它感动人们的,一定不是五体投地磕头去拉萨的信仰心,而是普通人的情感,感动在磕头之外,又不能脱离磕头,即故事既探入普适性人情微妙处,又发轫于藏族的特殊文化。
“阿拉姜色”是藏语音译,意为“请您干了这杯美酒”,大概是男女主角罗尔基和俄玛吃饭喝酒时唱的那首藏族民歌。
这种情调,加上从头至尾的伤感配乐,奠定了平静、忧伤甚至粘稠的电影氛围。
故事从俄玛清晨的哭泣开始,罗尔基不知她的梦,也不知她的秘密,但他至少能从“煨个擦擦”这种藏族祭奠死者的小仪式中猜测妻子的心事,并追溯到妻子隐瞒的绝症秘密,大叔憨厚,但不傻。
但妻子亲口讲出,她磕头上路去拉萨朝拜,只是为了圆死去的前夫托来的梦,临死也要嘱托他让孩子带着他爹的擦擦做的书包——即作为个体的信物——去拉萨,大叔遭受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
于是我们非常理解他听说妻子执意“死在路上”的缘由是她对前夫的爱之后那种妒嫉、失望,也理解他听寺庙里的和尚说,两夫妻一起升天,命真好,之后,不甘心地把照片撕成两半,分别贴在墙上。
孩子把照片拼回来随身带着,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在这个三口之家永远处于局外第四人的位置。
妻子爱的是前夫,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妻子的错,孩子爱的是亲生父母,不爱这个后爹,更不是孩子的错。
如果爱之伤是一个恒定值,总是需要一个人承受,那么善良的罗尔基就是那个注定受苦的人。
人一陷入这种局面,往往会叹息命运。
下一步,就是信仰。
无论是完成他所爱的俄玛随前夫的亡灵、磕头去拉萨这个遗愿,还是化解痛失所爱的悲伤,甚至与极少见面的继子建立相依为命的新关系,他都只能选择在这种关于信仰的仪式中体验过程,获取心灵平静和活下去的动力。
结尾处,目的地拉萨胜利在望,罗尔基与继子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即“我懂你的伤痛与情感,你的心里从未有过我,但我要陪伴在你身边,你是自由的”。
由此,他也终于能含泪接受“人家”两夫妻一起升天的冥冥之意。
大叔的泪,也为你我他而流,这不就是我们在爱中的处境吗?
3 ) 爱
可以算是我身为藏族人看的第一部藏族题材电影。
是上课的时候老师放的,本来没抱多大的期待,但是看着看着就令我动容,落了很多泪。
因为下课后我要马上去彩排舞蹈,不能让我看起来哭过,而且哭多了妆也会花,我就马上打开手机让自己转移注意力。
然后晚上回到宿舍把剩下的部分看完了。
不知怎的,这部电影特别特别打动我,可能因为我也是藏族,里面有很多能让我共情的细节吧。
电影从女主奄奄一息开始我就一直哭到最后,且久久不能平静。
罗尔基这个角色平凡又伟大,他深沉温柔地爱着俄玛,他骨子里的善良、爱与责任使他拥有跨越盛夏到严冬只为替妻朝圣的力量。
但他也会因妻子对前夫念念不忘而吃醋,也会因诺尔吾不听话而生气,可是这些都使他这个人物更立体,更可爱。
说说演员,前面我还真没看出来是容中尔甲演的,没想到他居然会演戏,且演的还不错,完全没让人出戏!
还有那匹小驴真是太可爱了。
4 ) 一部被低估的藏语文艺片!拉萨朝圣,治愈苦难!简单纯粹、有爱有信仰的温情之作!
打算找一部应景的影片看看,于是,最终挑选了这部《阿拉姜色》。
阿拉姜色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请您干了这杯美酒,它是来自藏区传唱已久的一首藏语祝酒歌。
《阿拉姜色》粗看像是一部藏民磕头朝圣题材的公路片,其实不然,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
影片讲述了妻子俄玛向丈夫罗尔基隐瞒了自己身患绝症的事情,执意要去拉萨朝圣。
罗尔基知道真实情况后,劝已经上路的俄玛返回,并想带俄玛去成都大医院治病,遭到俄玛的拒绝。
罗尔基没办法,只能陪同一起前往拉萨。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俄玛与前夫的儿子诺尔吾。
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俄玛因病去世。
在妻子的弥留之际,罗尔基才知道妻子为何执意要带病前往拉萨朝圣,连病都不愿意看了。
原来俄玛心里一直深爱着前夫,为了在死前能兑现与前夫去拉萨的诺言,不顾病痛折磨,带着前夫的“擦擦”踏上了朝圣之旅。
并且俄玛希望罗尔基能带着诺尔吾继续她未走完的路。
罗尔基是一个朴实的男人,他因为妻子心里还有前夫而生气,可是他也是一个善良的男人,或许他的内心也斗争了许久才下的决定。
不管是因为信仰,还是因为爱,最终还是带着诺尔吾走完了妻子剩下的路程。
妻子因为对前夫的爱,在身患重病后执意要去拉萨朝圣,罗尔基因为对妻子的爱,带着继子帮妻子走完未走完的路,诺尔吾因为对母亲的爱,在罗尔基要将他送过去的时候,他不肯,执意要跟着罗尔基一起去拉萨,完成母亲的心愿。
不仅如此,罗尔基与继子诺尔吾的情感也是微妙的。
诺尔吾从一开始的排斥到最后一直跟随其后,也表现了他对继父从一开始的排斥到最后的信任。
罗尔基告诉诺尔吾,作为一个男人,不能总跟在别人的后面。
最后快要到拉萨时,罗尔基给诺尔吾理了发,穿戴整齐,准备挑一个好日子在去拉萨。
理发的这个片段有点感人。
罗尔基帮助了妻子完成了她与心爱之人的诺言,在这里我们是有一丝心疼罗尔基的,但是这也体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
原有隔阂的一家三口,从四姑娘山下的嘉绒出发,磕头前往拉萨。
有人说,进藏的确不能净化心灵,朝圣的确不能不药而愈,信佛也的确不能万事如意。
但是,一条川藏线使他们的内心得以相通,也使他们的血液得以融合。
是的!
西藏之行完成了俄玛前夫的心愿,也完成了俄玛的遗愿,同时也让诺尔吾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让村民弥补了年少不懂事的幼稚,还让没有血缘关系的罗尔基和诺尔吾产生情感的羁绊,当然,最后也让罗尔基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很多人都说这部影片比《冈仁波齐》好看,我没看过《冈仁波齐》。
但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阿拉姜色》其实里面的元素很多,不光是朝拜和信仰,还有有关生与死方面、夹杂着许多家庭元素、路人的相助这些人与人之间情感方面、父与子的成长等等。
这部片子还是很不错的!
简单、纯粹、温情、有爱!
电影:《阿拉姜色》国家:中国大陆上映:2018导演:松太加主演:容中尔甲、尼玛颂宋、赛却加豆瓣:7.6=====2024年,继续我的1000部电影计划!
大家好,我是亿亿!
今天给大家推荐1000部电影的第150部:《阿拉姜色》-over-
5 ) 专访松太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文 | 何俏也(四年央视记者,一个写字的 b站:何俏也 微信公号:Pandora612星球)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有两部中国影片入围:《找到你》与《阿拉姜色》,最终,《阿拉姜色》荣获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及最佳编剧奖两项大奖。
《阿拉姜色》由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携手尼玛颂宋联合主演,讲述一个女人隐藏自己的病情,与前夫之间的秘密决定去往拉萨,在漫长的旅程过程中她内心的秘密被一一解开,这些秘密包含着她与前夫、丈夫之间的爱与道德,责任与信仰的纠结与困惑。
评委会赞誉这部影片“该电影坦诚而深刻,勇敢不妥协,描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刻画了在面临生命终极问题时刻的希望和救赎。
”导演松太加在获奖感言中说到:“特别淳朴,故事没有很炫的东西,因为还是接地气。
感谢我生活的那片土地,它给了我那么多源源不断的灵感,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
▲松太加松太加出生于安多藏区,是一名藏族电影摄影师、编剧、导演。
曾以美术和摄影身份参与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获奖影片。
2011年开始以导演和编剧身份参与故事片拍摄,作品有《太阳的总在左边》《河》《阿拉姜色》等。
“阿拉姜色”是嘉绒藏区的民歌,意为“干了这杯美酒”,导演松太加介绍,故事的缘起来自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而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是希望传递一种大爱,超越地域和宗教,“爱的诚信,爱的包容和爱的担当。
”制片人将《阿拉姜色》形容为一部“公路片”,三个月时间跨越了三个省份的朝圣路,对于一部小成本电影来说困难重重。
近年来,西藏题材影片逐渐走进观众视野,万玛才旦的《塔洛》,张杨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都获得了业界好评与艺术电影爱好者的关注松太加感慨,过去的确没有想过藏族题材电影可以有这么广泛的观众,“过去有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新疆电影制片厂拍一些民族电影,但也都是用汉语拍。
以前西藏好像只有我和万玛才旦两个人拍电影,但现在,有非常多喜欢电影的藏族年轻人都开始做电影,全国各艺术院校影视专业也能看到来自西藏的学生。
”专访松太加导演:1、您在这部电影中是怎样来处理藏族地区特有的文化习俗?
拍自己本民族的题材,您的优势在哪里?
松太加:这个故事像是风一样,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很想把这个故事落到另外一个点上。
我把它做成一个类型化的,类似于公路片的那种感觉。
但我希望电影能超越地域,回归到一个人的层面。
因为那片土地上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人为生活奔波,为生活发愁,然后依然对世界抱有希望。
这是有一个共性的,而不是它以往的贴着佛教标签的、或者是神秘化的一个理解。
2、这部电影的灵感是从哪里得到的?
故事的原型是什么?
松太加:其实我们创作的那个兴趣点还是比较喜欢家庭里的东西。
这次的电影里的男演员容中尔甲,他是藏区特别有名的一个歌手。
有一次我去四川,我们在酒桌上面聊,聊到他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无意间我说这个特别适合拍成一个电影,然后呢他也觉得值得写下去。
回去以后,一个多月这个剧本就写完了,写完了以后我给他发过去,他特别感动,要拍这个片子。
缘起就是这样。
《阿拉姜色》是藏族里的敬酒词,意思是下面请你干了这杯美酒。
我希望这部电影是我精心酿造的一杯酒,我现在把它端出来想跟大家分享。
▲《阿拉姜色》剧组3、您受哪些导演的影响比较大?
松太加:我说我喜欢是枝裕和,他好像是太流行了,但是很多年以前我就看是枝裕和,特别感动。
还有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但是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更符合东方的一种表达方式,特别符合藏族人的对亲情、对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
我的电影里没有那么激烈的感情传达,一点也不疯狂,是一种含蓄的感情。
就没有那种男人大哭啊这种。
我们藏族人是不会当着一个人说我爱你啊这种起鸡皮疙瘩的话。
包括我父母结婚了差不多40年,但是他们一生都没有说过一个爱字。
爱这种东西实际上很温暖。
感情不是挂在嘴上的,那样它太廉价了。
6 ) Sonthar Gyal, réalisateur tibétain : « la vie ordinaire des Tibétains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passionnant »
Sorti en VOD le 11 novembre en France, Ala Changso, le troisième long- métrage de Sonthar Gyal, brosse un portrait subtil et délicat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sur fond de spiritualité et de traditions tibétaines. Entretien.
Tous les films de Sonthar Gyal sont nés d'un dilemme familial. Concernant Ala Changso, sorti en 2018 en Chine, il s’agit d’un triangle amoureux : une femme meurt en plein pèlerinage, son mari découvrant dans le sac de sa femme une photo d’elle et de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Après tout, la vie est une affaire d’hommes, de femmes et d’histoires familiales. C’est pareil dans le monde entier », déclare Sonthar Gyal. Surnommé le « Hirokazu Kore-eda » chinois, ce cinéaste quarantenaire, né dans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Qinghai, était initialement cadreur et directeur artistique. En 2011, il s’est lancé dans la mise en scène, réalisant son tout premier long-métrage, The Sun Beaten Path, sélectionné et primé dans plusieur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River, son deuxième film, a été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e très célèbr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Berlin en 2015. Aux côtés de Pema Tseden et Lhapal Gya, il fait figure de proue dans la « nouvelle vague tibétaine », un courant cinématographique né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en Chine. Conteur des liens du sang et du cœur, Sonthar Gyal dépeint, à travers Ala Changso, un Tibet ordinaire, où les pèlerins, extraordinaires, sont prisonniers de leurs tourments intérieurs.Quel a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u film ?Sonthar Gyal : Ce sont les financeurs qui m’ont proposé de réaliser ce film, basé sur une histoire écrite par l’écrivain tibétain Tashi Dawa. Je l’ai accepté à la condition que je puisse modifier le scénario. Dans la version originelle inspirée d’une histoire vraie, un vieil homme part en pèlerinage jusqu'à Lhassa, et finit par nouer une grande complicité avec l’âne qui l’a accompagné tout au long du voyage. Avec l’autorisation de Tashi Dawa, j’ai réécrit le scénario, ne gardant que cet âne. Le nouveau fil conducteur porte sur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entre une femme, son fils (né d’un premier mariage) et son deuxième époux. Il est connu que le road-movie est un genre toujours en mouvement, ce qui constitue un défi d’écriture. Néanmoins, la dynamique conflictuelle de ce trio permet de créer des rebondissements dans l’intrigue.Comment qualifiez-vous les troi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Mes héros sont avant tout des gens ordinaires, sauf qu’ils ne cessent de se dépasser. Pour moi, le dépassement de soi et la tolérance envers les autres constituent les fondements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Ce sont également les points communs partagés par les trois personnages. Drolma souffre d’une maladie incurable mais tente avant tout de réaliser la promesse faite à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Dorje se dépasse en poursuivant le pèlerinage à la place de sa femme afin de tenir sa promesse ; Norbu, le fils très têtu, finit par se rapprocher de son beau-père.Ala Changso est le titre d'une chanson à boire. Pourquoi l’avez-vous choisi comme titre du film ?Je l’avais nomm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365 jours de Dorje. Il traite d’un sujet lourd, voire étouffant. Mais un film, comme un tableau, a besoin de prendre des couleurs. Lorsque j’ai parlé avec l’acteur principal Yungdrung Gyal, j’ai pris connaissance d’Ala Changso, une chanson à boire, très populaire chez les Gyalrong (un peuple vivant pour la majorité au Sichuan et parlant la langue gyalrong, dont font partie les héros du film). On peut aussi chanter Ala Changso sans alcool car ce sont les messages et les émotions qui comptent. Cette idée m’a beaucoup plu. C’est le premier rôle au cinéma pour le chanteur Yungdrung Gyal (Dorje). Comment s’est passée votre collaboration ?Comme Yungdrung Gyal, les acteurs de mes derniers films ne sont pas des professionnels. Les comédiens tibétains professionnels sont rares. Je les choisis souvent par intuition. Il faut que je calque sur une personne avant d’écrire un scénario. Pour Ala Changso, c’était à Yungdrung Gyal que je pensais. Mais il ne l’a su qu’au dernier moment, et il a paniqué quand je le lui ai dit. Il n’avait jamais fait de cinéma et n’était pas sûr de lui. J’ai fini par le convaincre en imposant une seule condition : il doit couper ses cheveux longs, portés depuis presque vingt ans. On était une centaine dans l’équipe qui comptait sur lui. Il était stressé lors du premier jour de tournage. Une situation que j’avais anticipée. C’est pourquoi j’ai pris du temps pour lui expliquer ce qu’était le jeu d’acteur et les bases de l'espace filmique. C’est quelqu’un de très intelligent, il s’est très vite adapté et s’est mis petit à petit dans la peau de son personnage, Dorje.Quel a été le plus grand défi du tournage ?Je suis originaire des contrées tibétaines, donc le climat de la région ne me posait aucun problème. Le film a été tourné en été 2017. Il a fait beau pendant les quarante jours de tournage. On a eu de la chance. Mais c’était quand même dur de filmer la dernière scène qui avait lieu dans la neige. Notre équipe était montée au sommet d'une montagne, bien au-dessus de 4 000 mètres d’altitude. Qu’est-ce qu’il faisait froid !Comment le film a-t-il été reçu à sa sortie en salles ?J’ai été surpris que le film ait connu un succès au Japon. Mais en Chine, même s’il a été bien accueilli dans le milieu du cinéma, le grand public n’était pas au rendez-vous. Je pense que les jeunes d’aujourd’hui, plus habitués aux vidéos courtes et aux films à effets spéciaux, sont trop impatients pour apprécier les films comme les miens. Mais il existe des férus de ce film, qui l’ont même regardé plusieurs fois.Le film est en tibétain...Il est en gyalrong, un des quatre dialectes principaux du tibétain. Ce sont les Tibétains vivant dans la préfecture autonome tibétaine et qiang d'Aba du Sichuan qui parlent ce dialecte. Ala Changso est d’ailleurs le premier film en gyalrong. Mais ni moi ni l’acteur principal ne parlons ce dialecte. Nous avons dû recruter un professeur maîtrisant le gyalrong qui vérifiait sur le plateau les dialogues pour chaque plan.Depuis la sortie du film Le Silence des pierres sacrées (2005), mis en scène par Pema Tseden, de nombreux films en tibétain ont émergé en Chine. Peut-on parler d’une tendance ?Après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1949, ce sont les sociétés d’État qui étaient chargées de la 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À cette époque, les films sur la vie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étaient tous en mandarin, ce qui était en-soi ridicule. La langue, essentielle dans le cinéma, constitue une manière de penser et une façon de voir le monde.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les réalisateurs tibétains sont nombreux à s’emparer de leurs histoires. D’où l'émergence de ces films en tibétain. C’est un nouveau phénomène, mais c’est loin d’être une tendance. Aujourd’hui, beaucoup de gens pensent qu’il est plus facile pour un réalisateur comme moi de remporter un prix du fait de la politique de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à l’égard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chinoises. Une logique qui ne tiendrait d’ailleurs pas la route dans le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Ce qui est un peu dommage car on n’évalue pas les films à leur juste valeur.Dans la culture mainstream, il existe de nombreuses représentations exotiques du Tibet. Y accordez-vous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pour ne pas tomber dans ce piège des stéréotypes ?Je filme le Tibet comme il est, ne renforçant ni ne contournant ces représentations dites exotiques. C’est ça le cinéma. Au Tibet, les gens ne portent pas tous des habits traditionnels. Par contre, ils ont tous un portable et comprennent parfaitement le mandarin. On a tendance à voir le Tibet à travers le prisme religieux et politiqu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e Tibet demeure un endroit sacré et mythique. Mais où sont les êtres humains en chair et en os ? Pour moi, la vie ordinaire des Tibétains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passionnant. Si j'aborde souvent la thématique de la famille dans mes films, c’est que l’intime et les liens filiaux constituent les fondamentaux de notre vie, quelle que soit la culture.L’étiquette « réalisateur tibétain » vous colle à la peau. Constitue- t-elle un avantage ou un inconvénient ?Je ne mets jamais en avant mon origine ethnique. Mais en Chine, on a tendance à renforcer cette identité, en témoigne notre carte d’identité, qui indique notamment le groupe ethnique auquel appartient le titulaire. Chinois han, ou Chinois tibétain, nous sommes tous des citoyens dans le pays. Pas la peine de faire de distinction. Il en va de même pour cette étiquette de « réalisateur ». Je ne parviens pas à l’assumer. À mes yeux, c’est un métier aussi sacré qu’abstrait. C’est pourquoi je n’ose pas me présenter comme réalisateur, préférant dire que je travaille dans le cinéma. Ce mal-être viendrait peut-être du fait que je suis devenu réalisateur sur le tard.Comment êtes-vous entré dans le monde du cinéma ?Originaire d’une petite ville, je me passionne pour le cinéma depuis que je suis enfant, mais je n’ai jamais pensé faire des films un jour. Après des études de beaux-arts, j’ai été instituteur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J'ai fait la connaissance de Pema Tseden et nous avons décidé de poursuivre des études à l'Académie de cinéma de Pékin. Il avait intégré l’école un an plus tôt que moi, et m’a conseillé de choisir la spécialité « image ». J’avais presque trente ans à ce moment-là. Au bout de deux ans de formation,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tourner des films.Est-ce difficile de tourner un film d’art et d’essai en Chine ?Au début de ma carrière, il étai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financements. Maintenant, comme plusieurs de mes films ont reçu de bonnes critiques, ça va beaucoup mieux. Tout d’abord, je peux garantir la qualité du scénario et en plus, mes films à petit budget ne font pas perdre de l’argent aux investisseurs. Aujourd’hui, c’est devenu un cercle vertueux. À vrai dire, les films à grand budget ne m’intéressent pas. J’ai peur de perdre ma liberté créative sous la pression des investisseurs.Quels sont les cinéastes ou les films qui vous inspirent le plus ?Les Garçons de Fengkuei de Hou Hsiao-Hsien a marqué un tournant dans ma vie. Je l’ai visionn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2003 lors de mes études à Pékin. Mon Dieu ! Je n’avais jamais vu un tel film. J’étais en transe durant le mois qui a suivi. Dans le film, les jeunes protagonistes se sentent piégés dans une ville qu’ils ont envie de fuir. Et petit à petit, leurs rêves ont fini par éclater comme des ballons. L’un se marie, l’autre échoue à devenir artiste et passe son temps à arpenter les rues de la ville. J’ai compris que le cinéma pouvait s’exprimer de cette manière. Pour moi, c’était une révélation.(去年隔离时微信采访的。
影片后劲很大。
)
7 ) 请喝了这碗美酒吧!
在看任何电影前我一般都不会看故事简介,也不会看预告片,选择影片全凭感觉,包括这一部电影。
起初只是想要支持藏语电影的票房,没有提前去了解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开始看没多久,俄玛(女主角)就提出要磕长头去拉萨,当时心里的念头就是怎么又来了,除了朝圣就没有其他故事可讲了么?
然而这种抵触随着影片的发展渐渐消失,朝圣不过是导演借助讲故事的一条辅助线而已。
从同行的朋友相继离开,丈夫知道病情反对她磕长头去朝圣,再到后来后父和孩子的继续前行,这条线的作用是让他们互相和解。
俄玛在影片开始时,从噩梦中惊醒继而哭泣,直到她快坚持不住时才告诉丈夫,梦里出现了什么。
这个时候她和前夫和解了。
叛逆的孩子和罗尔基一直心存芥蒂,在维系他们关系纽带的母亲去世后,罗尔基本来想送这个累赘回家,但是他曾对那孩子许下带他去拉萨的诺言。
看见拉萨的地标牌后,罗尔基没有忙着继续前行,说要休息几天收拾收拾,挑个好日子去拉萨。
在拾起驴打翻的骨灰盒时,看见他当时撕碎的照片被黏合放在里面,是他和死去的人和这孩子的和解。
和去年的《冈仁波齐》相比,这部的故事性好很多,并且加入了很多生活和民俗的琐碎片段。
俄玛知道自己病重,不愿意去大城市治病,因为她知道并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但我以前一直认为,去选择相信佛教可能都有自己的目的,比如这种状况下就可以期待一下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阿婆病重去世后,一度无法和信仰和解,想不明白这么善良和信教的人怎么会这么快离开人世。
近两年大概成长了,发现有的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个样子。
在我们那儿,清晨煨桑或者点佛灯时,都要双手合十许愿。
在今年以前的我,许的愿不外乎是关于自己或是家人的。
在藏历年去祈福时,舅舅跟我说许愿时应该要加上天下苍生,不能自私地只为自己祈祷。
在那以后,每次都留心听了一下别人的祈祷,真如舅舅所说,不管贫苦还是富足的人都在为天下苍生祈祷,突然就觉得自己眼界好低。
人们大都觉得自己不甚了解的这片高原神秘莫测,再加上宗教赋予的力量,甚至以为来了一趟就能“净化心灵”,拍了一些风光大片回去,生活照旧,不如意的仍然不如意。
其实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又有什么差异呢?
琐碎,反复,无聊,这不就是生活。
条件还比不上大城市,只不过欲望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每天做好分内的事情,除外能再转经和念点佛就是大多数人的要求了。
以前看很多藏语片,觉得太不真实。
艺术虽然要高于生活,但离开生活也不行。
少数民族在表达喜欢时都爱用酒,民间流传各种祝酒歌,电影里唱的便是其一。
高原上的冬天很冷的,只要不干活,大家都爱围在火炉前烤火聊天,再烤点土豆在炉灰里,烫到双手不断扔来扔去吹气,也不愿意放在桌上。
电影里最打动我的片段也是烤火,他们烤了好几次火,每一次故事都更进一步发展。
他们一家人围在火堆旁,罗尔基拿着一块石头假装是酒碗,唱起了“阿拉姜色若”,在传递的歌声中和解。
少数民族好像都能歌善舞,在表达情绪时便可以用歌声,最喜欢小时候和阿婆转山时其他老奶奶们用唱腔念经,此起彼伏,在诺大的山谷里回荡。
出生在这个地方好像蛮幸运的。
所以呀,有排片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不会后悔的良心之作。
8 ) 神啊,善良的人会有好报吗?
下午1点去看了这部电影,感觉很满足。
惊喜这是一部低调又内涵丰富的电影。
这几年以藏区为题材电影挺多,很多会以朝圣为主题进行创作,这其中难免有许多渲染的东西,比如将朝圣这个事件神秘化,夸大化,但这部电影却刻意避免这些。
故事讲述的是藏区一位二婚的妇女在夜里梦到死去的前夫,想起在其生前许下一起去拉萨朝圣的愿望,在随后得知自己病入膏肓的情况下,遂决定去完成愿望的这么一个故事。
电影全篇运用了大量的近景拍摄手段,把远处绮丽的青藏高原自然风光弃于不顾,旨在弱化自然环境对朝圣这件事的渲染效果,从而把精力主要分在故事线和人物上,这使得人物十分鲜活,饱满,同时也增加了影片的纯粹性。
藏区人民信笃佛教,十分善良,他们相信这一世虔诚地供奉活佛,不杀生,下一世就会有福报。
影片中,酥油茶灯淹死了一只飞蛾,男主就会惭愧地说,罪过呀,淹死了一只飞蛾。
说了这些,就迫不及待地想分享下主角们的故事。
俄玛,在六年前,前夫病死后,有一子的情况下改嫁到男主罗尔基家,身体不好的她时时记得病故前夫的愿望--出院后想让她一起去拉萨朝拜。
女主在得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情况下,瞒着自己的病情和家里人说要去拉萨朝拜,家人觉得这也是一件功德很大的事情,就同意了,但没告诉丈夫去朝圣祈福的真正原因。
在丈夫家里生活,孩子寄养在外公外婆家,一边要照顾现在这个家,考虑男主的感受,另一方面又要去考虑孩子在另一边过的好不好,就在这夹缝中生活着,左右为难,就连生命中最后一件事也不能说明原因就要独自去完成,虽然最后男主和孩子都一起加入朝圣队伍,但最终也没能完成愿望就陨于半道了。
对于这短暂、痛苦的一生,她就总结了两句话,一切都是缘分,一切都是命。
男主罗尔基,我最喜欢这个人物角色。
总体来说,是个很丧的人吧。
把家中断腿的老父亲交给乡亲照顾,都要决定花一年的时间陪妻子去拉萨朝拜,做她最坚实的后盾。
一起生活六年的人呐,到死的那一刻,方才告诉自己:罗尔基,我这次去拉萨朝圣,其实为了我死去前夫祈福,完成我和他生前的愿望,我死了之后,希望你带着孩子去拉萨完成这项功德。
男主就想,我做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换来这样结果,你拼命想去朝圣,就为了一个死去六年的人,还是你的前夫,而且一路你还随身带着你们的结婚照,男人的颜面往哪搁?
在寺庙给亡妻做超度的时候,不明真相的活佛还把照片上的两人以夫妻一起来超度,路上还有一个拖油瓶的继子时刻提醒着自己,这场功德呀,全是为了他那死去是的生父呀,这是真的扎心,真的丧。
一般的人就应该炸裂了吧,但男主并没有像一般剧情那样去黑化,做的最大的报复就是在供奉的时候,把这张照片给撕了。
我把这归结于男主笃信佛教的善,化解了这恨。
再来说说继子诺尔吾,穿着一件过膝的松垮垮的外衣,带着怨气,不和母亲、继父交流;在学校经常和同学打架,导致推迟一年入学;敢头戴塑料袋,站在大马路中间吓唬迎面疾驰而来的大货车,就是这么一个淘气的正太。
在母亲死后,只是麻木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看到路边的母驴死去,小驴的哀嚎,才让他忍不住崩溃。
对于那个不让自己和妈妈生活的人,他是怨恨的。
不能忘记继父在旅途上揪自己的耳朵,就算继父解释了这是一种父与子的游戏,他也不接受道歉。
在母亲死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要和继父一起把剩下的路走完,心想,这是我讨厌的人,我才不会让他舒服呢。
可在后来继父怕孩子想不开跳水,就毅然跳入水塘寻找,还不计前嫌给孩子治脚。
人心都是肉做的,剩余的路途上,这个无法无天的魔王也开始接受那个人父亲般的说教,并深以为然。
最后的一场戏我是最喜欢的,快到拉萨了,父子沐浴焚香,准备收拾洗干净,第二天去布达拉宫和小昭寺朝拜。
男主在给孩子剪头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亡妻和其前夫两人的结婚照,孩子开始哭泣(本来想把这偷偷捡回来照片藏好,不能再让继父伤心了),说,我想让父母在同一个寺庙里超度;男主哭着说,孩子剪掉的头发要藏起来,不要让人踩到,你父母的事情,等我们回去,给他们弄到一个寺庙里去(谁叫这缘分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呢)。
在男主的哭泣声中,整剧终。
导演很细节,每一帧都没白费,像这种还原藏区人民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电影,低调,不哗众取宠,真的很难得,看的很爽,赞。
9 ) 阿拉姜色剧作笔记
罗尔基是影片的主人公,在影片中他的人物形象最饱满,他的人物欲望是想要维持这个家,稳定而顺利的过完一辈子,而在尽力缝补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事实上并不理解这个家庭里自己的家人,最终通过亲自朝圣理解了自己的家人起:罗尔基的患病妻子想要去拉萨朝圣,罗尔基不理解,阻拦承:妻子执意要去,罗尔基仍然不理解,但跟着去转:妻子死了,罗尔基知道自己不理解了,决定完成妻子夙愿合:罗尔基到了拉萨,理解了影片在剧作上选取了红头盔和帆布帽来作罗尔基内心的转变。
在起的部分罗尔基始终戴着或拿着他的红头盔,头盔作用是保护,是罗尔基维持家庭的内心外化,可以让他被摩托车撞了没事,而且头盔圆润饱满,与周围悬崖峭壁有视觉上的对比。
在承的部分罗尔基换上了帆布帽,丢掉头盔,是他为维持家庭做的让步,保留帆布帽,证明他仍不理解。
妻子死后,罗尔基什么也不戴,叩拜,头贴地,他是在慢慢理解。
藏族人风俗是除神职人员不让摸头,用罗尔基的头部佩戴物来做戏,又与罗尔基居家、上路、叩拜有联系,是很妙的道具设计。
10 ) 接过你的愿望,我们继续出发
有些电影是不怕剧透的,表情,词不达意或者言不由衷以及不曾说出的话语,无可逃避的困境,无意承载情感却恰好出现的风景,这些都可以构成一部电影最本质的内核。
《阿拉姜色》是这样的。
女主人公俄玛做了一个梦,梦醒之后她去了医院,发现自己身患绝症。
梦的内容她不愿意说给丈夫,但是她决定要磕长头去拉萨。
丈夫试图阻止,但是却没有成功,加入了妻子的旅途。
同时加入的,还有俄玛与前夫的儿子,顽劣、叛逆、沉默寡言的儿子。
故事进行到1/2,俄玛去世了。
去世之前,她告诉丈夫,自己此行原是为了实现一个愿望,那是梦里前夫给予她的愿望,去拉萨。
于是乎,故事的主角死了,剩下的人是否要完成这个故事。
故事的法则要求他们必须继续,而人生似乎也有着这样的法则。
继续走下去是必然的,就如同死亡也是一种必然。
可如何继续,却可以选择,那是藏在人身体里的光。
后半段失去母亲的小驴子一同加入了旅行,不必给予特别的情节,也不必设计超出生活以外的冲突与醒悟,就将一切都交托给接下来的旅行与时间。
于是父亲、儿子和小驴子一同接过了逝去母亲的愿望,他们出发了。
循环开始,你给予我的,我亦会给予更多的生命。
干枯的草、下雪的天、蛮荒的山、公路、路牌、县城,以及看起来那样普通的布达拉宫,导演没有刻意选择风景,更没有给风景添加滤镜。
那就是原本会遇到的一切。
其实这部电影不一定非要看作是一部藏族电影,除却用磕长头这个标志性的形式串联起整个故事之外,它的内核是普世的。
与其将它和《冈仁波齐》做比较,不如选择《如父如子》《菊次郎的夏天》《一一》这些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关联的电影。
但既然能将它们放在一起,并且总会一次又一次被它们感动,那也许印证了无论族群、身份、经历、性别、肤色,身而为人,我们藏在身体里那些情感,总是共通的。
电影的名字《阿拉姜色》,其实是一首祝酒歌。
母亲曾向儿子在夜幕中唱起过这首歌,篝火将他们的脸照亮。
而当父子终成父子,进入拉萨前,父亲替这个没有血缘的儿子剪发,他不由自主又唱起了这首歌。
“阿拉姜色(我们来喝酒啊),这酒喝干,不能哟不喝……”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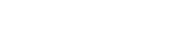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年度佳片#藏族同胞也有了值得自豪的导演了,很欣慰。本片给人很多惊喜,虽然故事单薄些,但细节工夫做的很足,人物有立体真实的生命力,感情有层次层层递进,完成度很高!这条信仰之路其实也是救赎之路,还顺带完成了夫妻、母子、继父子之间关系的修缮与升华,丧母的小毛驴更加深了主题,赞!
就这样吧……
用一个为亡者精神朝圣接力的情感故事透视了抽象信仰中的内在细腻纹理,手持长镜头的调度方式既记录了后景辽阔壮美的高原峡谷,也有触手可及的泥土流水,中段开始情感思路复杂而含蓄,神圣感轻盈地托举着父亲角色沉重的伦理隔阂。但同时对行程时间感和空间感的展现令人遗憾,即使是历时一年多的一千多公里的朝圣,仍给我一种在生动舞台上原地踏步的感觉。
如此真实
与冈仁波齐一路货色,藏传佛教从古至今到底处于什么阶层,从来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用子虚乌有的地狱话语来欺骗无知之人掩盖其剥削之实,最后还把这些被欺骗者的行为称之为虔诚,且无限的美化洗脑之,无耻,无耻至极!
艺术味道太浓,享受不了。能理解,但不能共情,电影不差,非我所好。
古怪淡漠男人,古怪顽固的儿子,奇怪的女人…没有一个可爱的人,在这个朝圣的背景下,莫名的开始了拉萨之旅……如果说男人爱女人第一反应不是带她去医院?
节奏有点慢,景色也不是拍得很美…剧情有点弱
还是冈仁波齐比较震撼我一点。今天下班去包了个场,说好听一点这种是小众文艺片,说难听一点,是我们忽略了这种真实的微小的生活,被流量明星和无脑捞钱片蒙蔽了双眼太久。
@2024-05-31 16:15:03
一般般 设定很奇怪。一个丈夫去完成死去的妻子的前夫的遗愿
3
3【兰陵幸福蓝海】在大家有意无意地神化着“藏人朝圣之路”的当口,松太加依旧着眼于最普世的话题和情感,将信徒的朝圣动机和行为完全私人化,圣地拉萨也只是在结尾处远远地打了个招呼。这种看似避重就轻的处理手法再佐以影片丰富的细节反而唤起了我们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强烈的共情,着实高明!
本质是个藏地公路片,没有一贯的神秘色彩十足,而是用纪实的手法去反映朝圣。母亲俄玛未完成的三步九叩首,由罗尔基父子去继续她的梦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拉萨朝圣过程中,熊孩子与继父,却逐渐产生羁绊。母亲重病去世,只剩他们相依为命。不是亲生,但浓郁的父子情,却依然打动人。容中尔甲演技还挺好,细腻而不浮夸。虽然有些平淡,这种题材无法大红大紫,却有着独特的价值。7分
Ala.Changso.2018.1080p.WEB-DL.AVC.AAC.mp4 2.39G
背身流泪,和开始的坐地大哭呼应,朝圣换来的宁静远胜过生离死别的痛
抛开藏族这个神秘包装,其实本片并算不上什么神作,可现在有了这一层光环之后,再加上些文艺,电影作品总是容易被神化,本片除了让人很意外的容中尔甲表演精彩之外,其他都比较平常
麻木的妻子,作死的小孩,病态的丈夫,牵强无说服力的人物动机,藏族题材不是非要浅到这种程度上才能表现宗教的虔诚,肖家河武侯祠玉林路我随便拉一对喇嘛摆龙门阵都能比这个更引人深思,干脆立个flag,有机会写个《当卓玛来到人间烟火之后》,拍摄地点玉林美食生活广场。
经此一片,容中尔甲已力压腾格尔,坐稳老哥汽车音响界的演技担当,唯有班霸韩红出演新版《爱奴》方可与之一决高下。
死亡赋予了夫妻感情独特的变动,男人由中心到局外,是溃败,由他者重回主线,缺乏润色,结局动人却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