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剧情介绍
菜埔(庄益增 饰)是一家雕塑厂的夜间保安,家中有一位重病的老母亲需要照顾。肚财(陈竹昇 饰)是菜埔唯一的朋友,菜埔经常在值夜班的时候把肚财叫过来和他作伴。一天,两人突发奇想决定看一看菜埔的老板黄启文(戴立忍 饰)的行车记录仪里记录了哪些影像,希望向来风流的老板能够贡献出一些精彩的片段以解两个独身男人内心里的寂寞之苦。 行车记录仪所记录的影像果然没有让菜埔和肚财失望,但与此同时,两人也发现了黄启文的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实际上,菜埔和肚财的一举一动皆没有逃过黄启文的眼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他决定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我太受欢迎了该怎么办看不见的朋友变态生理研讨会发明之父平民大英雄恋尸者法医秦明之血色婚礼风云Ⅱ不羁少年傻王闯天下行骗天下KR致命逃亡鹰眼美食大冒险之英雄烩为了皇帝音为爱致我的解离大奥绝望主妇第四季复仇计划爱之情照诺比特夜晚开的花夫妻吵架狗都不理,而查理笑了军旅轶事二见钟情宏观世界迷恋荷尔蒙芝加哥打字机一颗求偶的心
《大佛普拉斯》长篇影评
1 ) 《大佛普拉斯》观察小人物的视角是平视而充满爱意的
大多影视工作者说到底还是中产,如果没有真正在底层生活过,对小人物的刻画往往流于表面,或者总是带着自上而下的怜悯姿态,因此刻画出来的底层世界往往阴暗悲惨。
面对这些悲惨也总是一副严肃的面目。
《大佛普拉斯》之所以特别打动我,是因为导演看小人物是平视的,而且充满爱意,所以他才能那么放松地戏谑。
他刻画的底层世界自有一套法则,里面的人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按照这套法则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
所谓“苦难、贪污、社会阴暗”那些大问题,虽然每分每秒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左右着他们的命运,但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去关注。
有一处细节让我特别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视角。
肚财被警察抓捕之后,误会解开了,警员放了他,临了还不忘给他一个便当,让他带回去吃。
在小地方生活过的人是知道的,熟人社会,邻里街坊,即使立场不同(你是警我是匪),也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可能只记得你是一起上幼儿园的伙伴。
导演本来就反对媒体叙事中“警察大斗嫌疑犯”这种过分戏剧化的呈现,他想展现的是这个小世界自然的秩序,甚至是其中零星的温柔。
便当拿回去吃导演的平视也可以从他的旁白看出。
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和主人公一样通俗的、插科打诨式的语言。
他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浑然一体,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同情劳苦大众的感怀,而是一种工友聊八卦式的描述。
比如:
这个工厂大家都很关怀对方的老母再比如导演嘲笑警察的镜头,“我们的影像不像警方那样晃来晃去,毕竟拍片是我们的专业,晃来晃去的摄影师,早就发一个便当让他回去了。
” 这种表述很贴合主人公的逻辑,就像主人公觉得拍黄色杂志的摄影师应该得诺贝尔摄影大奖。
要知道有好多大片还故意花钱做出那种晃来晃去的特效,因为看起来“自然”。
但在门外汉看来,这些造作的“艺术风格”不过是技术不过关而已。
导演的旁白借用了小人物这种天真朴素的视角,来尽情地嘲弄知识分子,让人忍俊不禁,又因为带着一种间离和陌生化的效果,反而让大家觉得旁白(和小人物的观点)大智若愚。
最后就是一些对白和情节的巧妙设计,让每一个小人物的形象变得极其鲜活。
我想,如果导演没有因为拍纪录片或者其他原因和这些人真正生活在一起,是捕捉不到这种细节的。
比如片子最后肚财的葬礼,大家居然找不到一张肚财的照片,最后用了警察抓人的画面。
看到这里,本来泪水涟涟的我差一点没有笑喷。
仔细一想,又觉得不能更真实。
农村里老一辈的人,本来就是要到年纪大了临死才会想到要拍遗照,像肚财这样意外横死街头的穷苦人,怎么会备好照片呢?
再比如肚财和菜埔发现老板天天风花雪月,感叹老板真是好身体,最后评价一句“身体有在练”,差点没把我笑死。
听起来大智若愚的小人物导演刻画的这一批小人物,虽然生活艰险,却从来没有声泪控诉,反而有一种安于天命的平静。
比如肚财感叹启文老板好命,有留学,又有钱有势,还有漂亮的老婆,菜埔却只说了一句有钱又怎么样,一天还不是只吃三顿?
这份安于天命的平静和“豁达”,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自我安慰,让人心疼,但这却是菜埔等人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
这些人身处苦难却不自知,也不怨天尤人,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的苦命而感怀,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种“本分”更让人心酸呢?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嘉年华》,也是我很喜欢的片子,也刻画了很多小人物。
但单就小人物刻画这一点,我似乎更喜欢《大佛普拉斯》一些,原因就是导演对小人物的平视和爱意。
《嘉年华》里也有很多小人物,比如成天跳舞不关心女儿的妈妈,比如害怕生意被毁的酒店老板,比如小混混小健,他们都被生活摧残地变了形,被迫成为了“恶”的一部分,成为了“恶”的帮手。
但这些人除了悲惨以外,缺乏可爱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他们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停留在“抱不平”的阶段,停留在对“恶”的愤怒上。
《大佛普拉斯》比“抱不平”更进一层,是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这份理解依然有对不公的愤怒,但更平和,也更有悲悯意味。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总是不自主地想到爷爷奶奶的村庄,村民有善良淳朴的一面,但家长里短吵起来但时候,也有丑陋的一面。
他们生活艰难却依旧平静地活着,经历每一天的喜怒哀乐,插科打诨。
我想,导演对这样的世界有一份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理解和关怀,所以才能在这个外人看来悲苦的世界里,注入了那么多爱,那么多温柔。
比如肚财放满娃娃的床铺,比如那户给肚财夹菜、给犯人做饭的人家,甚至释迦身上穿的这件衣服,都赋予小人物以尊严,写满了导演对这个小世界的爱。
带着花环要去夏威夷的小乌龟
2 ) 我们如何观看?|评《大佛普拉斯》
相信任何看过《大佛普拉斯》的朋友都会对其戏谑幽默的叙事和对社会议题的深入探讨印象深刻。
不过,毕竟《大佛普拉斯》的获奖和映出已经有些时日,我们不妨先一起回顾一下开头的剧情。
故事发生在某个位于台湾中南部的靠海的乡村。
影片的开始是一场葬礼,在送葬队的前方,我们与影片的第一位小人物菜埔相遇。
当然,生硬的敲鼓姿势和无节奏感的鼓声告诉我们,送葬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事实上,对于有一个病重的母亲需要抚养的菜埔而言,送葬队的收入实在太少。
夜幕临近,菜埔的“正式就业岗位”浮出水面——他在一家正在制作大佛的工艺品厂守夜。
不过,保安室的夜晚并不孤单,因为村里进行“资源回收”的“个体户”肚财几乎每晚都会如约而至,跟菜埔喝茶聊天,运气好还能吃到便利店扔出的过期便当。
原本,那天晚上只不过会是肚财在保安室边看电视边吃便当的寻常时光,但很遗憾,“下饭”的电视机坏了。
无聊之际,肚财打起了菜埔的老板启文的行车记录仪的主意。
一番鼓动之下,菜埔也没抵挡住诱惑,就拿来启文旧奔驰的行车记录仪,开始从这些音画分离的录像中为燥热烦闷的夜晚寻找快乐。
第一种观看:从黑白看向彩色讲到这里,我们先停下对于剧情的直接的线性叙述。
因为一个有趣的设定出现了。
在这部黑白影像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彩色的图像——当然是在行车记录仪里。
肚财甚至自觉的感叹,只有有钱人的世界才是彩色的。
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影片的第一重观看,黑白世界中生活在底层的菜埔和肚财借由行车记录仪开始观看启文的充满着图像和欲望的实现的彩色世界。
这种观看是以某种娱乐化且猎奇的窥视开始的。
我们不能忘记肚财想要观看行车录像的原因是电视机的损坏。
如今人们已经基本认可了电视作为一种重要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通过这个小小魔盒我们可以单向的、被动的去获得形形色色的信息,尤其是人们最喜欢的情节剧、花边新闻等等。
毫无疑问,行车记录仪是某种电视的替代品,而菜埔和肚财也确实想在行车记录仪里寻找本想在电视里面获得那些与他们生活无关的却又确实期待着的东西。
行车记录仪也确实给出了一些期待,他们看到了那些也能在电视中看到的上流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物欲横流:色情的“图像”、狗血的故事和若隐若现的黑金政治。
然而,老板的行车记录仪与电视媒介却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
行车记录仪所展示的世界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有着直接的、明确的关联,因为行车记录仪的拥有者,“节目”的主演就活在他们身边并且直接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菜埔和肚财开始观看启文现在正在使用的奔驰车的行车记录仪式,他们被迫要与现实遭遇了。
这个时刻开始于菜埔在行车记录仪的彩色世界里看到自己为老板开门的那一刻:他在彩色的世界中认出了自己(插句话,这个隐喻曾经在肚财身上也类似的展现过:他的朋友们在新闻里看到了他被警察扣押)。
他们不仅目睹了启文谋杀威胁他的前任情人并藏尸大佛的全过程,而且得知了启文与当地政商界更加肮脏的肉体和利益交易。
摘下假发的启文 这种“相遇“的直接结果就是二人观看时的享乐机制被剥离。
布尔乔亚们由于他们的权势而遭遇的“奇闻异事”或“丑恶行径”的娱乐猎奇效果,仅仅在我们认为它们事不关己时才会起效。
因为这些奇谈的真实性往往就意味着与我们同样的人们的真实的、具体的苦难经历。
换句话说,菜埔和肚财被迫意识到,他们惧怕又羡慕的温文尔雅的“留美头家”不仅确实参与了权钱交易,而且还在他们熟悉的场景内杀人并藏尸。
残酷的社会结构暴力显现了出来,正如儒雅的启文在杀人时不慎露出的秃顶一样。
更重要的是,菜埔和肚财在这样的暴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这一方面体现在肚财所说的“你不知道警察局和法院都是有钱人开的吗”,更耐人寻味的则展现于事发之后启文来到保安室与菜埔的交谈的场景。
这段对话中基本看不到对话常见的正反打的过肩镜头,而是在大多数时间,启文都占据了画面的中间位置并接受了几乎所有光源,而懦弱的、不善言语的菜埔则“蜷缩”在画面右侧的阴影之中。
即使忘记了具体的对话环境和内容,观看者都很难忘记启文特意摘下假发来询问菜埔的那几句话。
统治阶级根本就不惮于展示自己的真面目——当然那是因为顺带展示出来的是真正的权力。
而且正是这种权力,让我们敢怒不敢言。
第二种观看 回望黑白中被压抑掉的彩色潜藏在行车记录仪的秘密并没有将故事引向一个为真相而抗争的,有关草根英雄的悲剧。
彩色的消遣消失后,黑白世界的生活仍在继续。
后续的故事发展提示了这部《大佛普拉斯》的另一种观看。
在具体论述以前,我想先澄清一点,虽然我用了“后续故事“这一描述,但这样的观看模式和视点是从影片始至影片终的。
作为观众,我们一直在同时观看着彩色和黑白两个世界,并且同样带着某种猎奇、寻谜的视点进行着观看。
翻看豆瓣的影评,许多人都在短评提到了“听书”之感:谐谑的旁白熟练地游走与间离的剧情之间,提示着我们剧情的荒谬性和电影本身的再现性(换句话说,这是电影,不是生活本身)。
如果说,在电影剧情外这个视点是导演的旁白带领下的观众的视点,那么在电影故事内,这个视点就是大佛的视点。
行车记录仪的秘密被揭开后的故事中,这样的视点及其观看方法开始重新取得了支配地位,而观看的对象变成了黑白世界。
在此之前,菜埔和肚财以及那位在本篇评论中至今还未介绍的另一位流浪汉“释迦”,都是有些“单薄“的。
我们知道他们是底层,他们弱小和无助却又有一些些与众不同(比如,肚财喜欢抓娃娃)外,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开始了解肚财更多,一点点有关他的过去,至少知道他去北方打过工,他坐过牢,但还没等我们了解更多,他就因为醉酒驾机车而(“被撞死”)消失在人世。
这场悲剧性的、有些荒诞的死亡也牵扯出了更多有关菜埔和肚财“隐藏剧情”。
我们首先知道了菜埔有个小叔,但他明显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也不可能接受帮助自己照顾母亲的请求。
菜埔在肚财家的“太空舱”里最后,我们终于进入了肚财生前的房间,这里意外的干净、宽敞和整洁。
我们同时也知道了肚财这样一个“收废品的”有一个太空舱一样的床,上面摆着娃娃,贴着捡来的杂志上撕下来的美女插画。
在这一刻,我们终于等到了那句似乎期待了许久的旁白:“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看到了一些被压住的丰富色彩的可能性,却也看到它们注定被遮蔽的命运。
我们因此而要直面:一个玫瑰色的生活是存在的,但它似乎只出现在每个人的不可见的内心的小世界里。
而在公共的、主体间的生活里,只剩下灰色的孤独、无意义和人与人沟通的不可能性。
更进一步,法会上的佛像精美,但善恶却无报;人们诵经念佛,却说不出彩色的音符。
视角之外,我们还能理解些什么?
视角和观看方法的变换,不免让人想到布莱希特戏剧间离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黑白/彩色的对立,可以看到对于电影仅仅是“再现的提示”(导演的旁白),我们也看不到英雄式的主角。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刚刚所提到的两种观看的视角结构出了剧情中潜在的两条线索。
经由黑白/彩色的区分下黑白世界中的人物对彩色世界的观看,阶级的隐喻产生了;而经由观众对整个故事中黑白世界的观看,有关生活及其意义的存在主义的反思的隐喻浮上了水面。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两层隐喻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从从导演的访谈、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是电影本身,这两层隐喻是紧密关联且无法分割的。
拆解掉任何一层隐喻,剧情及其意义就会发生根本地变化。
一方面,孤独与人际沟通的“不可能性”、生活意义的失语和“善恶有报”的失效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而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的暴力不仅仅是某种叫“结构”的抽象物的暴力,同时也是具体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就像屏幕前林林总总的奇闻轶事背后是真实的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
《大佛普拉斯》的观看模式及其隐喻结构有趣的是,豆瓣中的许多热门影评里反思的重心都落到了存在主义式的痛苦。
或者即使谈到了有关阶级与底层的话题,也用着置身事外的态度遣词造句,真正站在了“大佛”理中客的视角。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视角在影片外难免最后滑入了委员、副议长、启文的视角。
菜埔、肚财对于大多数观众和大多数甚至没有时间和途径看这部电影的人来讲,与其说是他者,不如说是镜像——失意的北漂青年和懦弱的下岗再就业人员。
那么释迦如何呢?
如果从大多数的影评和评论来看,释迦更多地被误认为观众们的理想的镜像。
释迦是一个流浪汉,但是他爱干净:穿的干净、住的干净。
他没有过去的负担,也没有未来的期许,只是不断的在村里“逛一逛”。
他如果真实的存在于现在的上海,就是一个爱干净且更深沉的杨高南路的“圣沈巍”。
黄导在一次演讲中确实谈到,释迦意味着另一种可能的活法。
但我不得不用《大佛》的剧本的潜在结构帮他补上一句,这样的活法在彩色世界的支配之下只能是个别的甚至是纯粹想象的:没有人可以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
当然,我这绝对不是在责怪和贬低《大佛普拉斯》的艺术成就,相反,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已经用独特、有趣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技巧为我们再现了一些生活中的困局。
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艺术的特性是使我们“觉察到”某种暗指现实的东西,它不能代替理论的认识本身。
所以,进一步的反思和批评,应该是我们观众自己的任务了。
参考文献:[1]阿尔都塞,2011,《论布莱希特与马克思》,陈越、王立秋译,《文艺理论与批判》第6期。
[2]阿尔都塞,2010,《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载《保卫马克思》,顾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21-144页。
[3]阿尔都塞,《一封论艺术的信》,https://www.douban.com/note/446379109/
3 ) 《大佛普拉斯》是如何刻画小人物的?
关于黑白和彩色的误解看很多评论认为片中的黑白代表底层人的生活,彩色代表上层有钱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
君不见,片中池子里KTV一段是黑白的吗?
启文兄车里冲浪也是黑白的?
那位师姐带着僧人见大佛一段也是黑白的?
其实,真正彩色的镜头都是行车记录仪录下来的片段,也就是肚财和菜埔两个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行车记录仪监控录像片段。
行车记录仪是个好东西,你可以听到车里人的声音,看到记录仪拍下的车外镜头,却看不到车内的场景,车内的画面需要你脑补,去根据声音想像,这里导演就有点双关的寓意了。
黑白是现实的世界,无论是穷人和富人,而彩色的片段则意指底层人小人物所幻想的有钱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4 ) 肚财是被启文杀的吗
电影中,肚财的死被警察判定为:过量饮酒,然后被撞死了。
大家都知道,肚财从不喝酒,而且一般都是喝酒的撞死人,哪有喝酒的被撞死的,最重要的是,肚财还是一个买不起酒,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的穷光蛋。
作为观影人,有着上帝视角的观影人,大家的直觉,几乎认定了是启文杀死了肚财。
在这个认定下,有人甚至已经提出了电影中的一个bug——启文是怎么知道肚财他们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bug。
因为在我看来:肚财真的只是死于一场意外,和启文并没有直接关系。
而警察为什么给肚财的死一个荒诞的结果——因为肚财就是一个死了的流浪汉啊:没有证件,没有家人,没根没枝,静悄悄地死去,不会有人追究他的死因。
对于这样一个流浪汉的死去,和死去了一条野狗有什么区别,警察为何要浪费精力去查他死亡的真相,直接给一个醉酒,盖棺定论,多么省事简单。
要知道,警察的摄影机可是会晃来晃去的。
让一个买不起酒的流浪汉死于醉酒,不就是和晃来晃去的摄影机一脉相承!
以上观点,是出于警方角度。
我为什么认为肚财的死和启文没有关系,因为启文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你看,启文被警察约谈后,回来走到菜埔的值班室。
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这个房间了,然后眼睛却看向电脑的监控画面。
很多年没有进过这个房间,言下之意可以理解成:他没有来过菜埔的值班室,所以不知道这里的监控可以看见哪些角落。
他杀叶女士的那个晚上,菜埔值班室里的监控电脑,到底有没有拍到些什么。
他拿下假发,说自己很多年没有拿下过假发(杀叶女士的那晚假发掉了下来),问菜埔是否看过他这个样子,菜埔点头摇头,含糊不清。
在我们观影人的上帝视角里,知道是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启文杀人的过程,而在启文的视角里,他根本就没有往行车记录仪这个方面想过。
他在菜埔的值班室关注的:是监控器是否拍到了他杀人!
菜埔是否通过监控看到过什么!
或者那个晚上,菜埔有没有听到什么响动,看到些什么!
你看他对菜埔的说话顺序,先是关心:工资是否够用,房子漏水,母亲生病;接着拿下假发问菜埔是否见过;得到菜埔含混不清的回答后,他开始施威:你上班的时候打瞌睡,你捡垃圾的朋友经常来这里找你聊天......恩威并施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上班不认真的事我都知道,但我不会炒了你,所以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什么,都给我烂在肚子里,别去外面胡说,要是被我知道了,你知道下场。
在启文的视角里,他怀疑的对象,其实一直都是菜埔,根本不是肚财,就算要杀人,他也会杀菜埔,而不是肚财。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启文关注的重点是监控器,并没有联想到行车记录仪?
如果启文联想到行车记录仪,看过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视频,就会知道行车记录仪完整地拍下了他杀害叶女士的过程,这可是直接的、致命的、关键性的证据。
如果启文知道了菜埔和肚财看过他的行车记录仪,这两个人算得上是亲眼目睹了他行凶杀人,关键他还不能保证他们是否拷贝了一份,他又怎么会只杀肚财,不杀菜埔呢?
有人说是因为菜埔有母亲可以威胁,肚财找不到把柄。
拜托,如果启文知道了菜埔和肚财看过他的行车记录仪,他怎么可能因为有什么可威胁的就留下一个“目睹”了自己杀人过程的人!
要知道,启文可不是什么心理素质强大的人。
在胖胖的女士说佛相不对称,不够庄严的时候,启文在一旁不停地擦汗。
注意,这个时候,胖胖女士还没有提议要把大佛锯开重塑,启文已经因为心虚紧张,不停流汗了(因为大佛里面装着叶女士的尸体)。
以启文的性格,如果他知道菜埔看了行车记录仪,肯定菜埔“目睹”了他杀人,这个威胁,他是绝对不会留的。
参见他对叶女士动杀心时,正是叶女士拿她拍摄的监控视频威胁他。
同样的,菜埔和肚财虽然提过他们是不是要去报警,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报警。
他们手上拿着的,可是启文的杀人视频。
如果他们报了警,启文怎么可能只是被约谈个话而已?
换言之,菜埔和肚财,把他们看见启文杀人的事情烂在了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即便土豆看出来他们遇见了不好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所以在启文的视角,他根本没有想过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什么(要是想到了,早就清理行车记录仪了,还会留着给菜埔和肚财看),他唯一担心的,是监控视频拍到了什么!
以上观点,出自启文视角。
很多人不解,启文找菜埔谈话后的那晚,肚财站在外面不敢进,为何会对这里产生留恋、不舍。
因为没过多久,肚财就死了。
在观影人的上帝视角里,直觉总认为这是肚财知道自己要被启文杀害的预感,这些话,像是一个将死之人对生的留恋。
这的确是肚财的留恋,但不是一个将死之人对生的留恋,而是一个“人”对生而为人,应当感受到的“尊严”的留恋。
他在菜埔的值班室,可以对菜埔高声说话——这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对别人高声说话的地方。
他和菜埔看启文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视频里的声色犬马,是他唯一最接近的富人的世界。
他在这里,才不再是那个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的捡垃圾的肚财,他才能微微跳出他黑白的人生,接触到一点彩色。
可是启文对菜埔说——我知道你那个捡垃圾的朋友每天到这里来找你聊天。
你想想,要是你朋友的老板对他说,知道你在朋友上班的时候,每天去他公司找他聊天,你还敢再去朋友公司找他吗?
那不是连累朋友丢工作吗!
并且,肚财来找菜埔,原本就有一点偷偷摸摸的意味。
启文杀叶女士的那晚,肚财和菜埔在值班室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听到启文的车响,肚财马上躲到了桌子下面。
他偷偷来启文的公司找菜埔,得知被启文发现,试想,肚财还敢再去吗?
他不能再来菜埔的值班室,就意味着他再不能来到这个他唯一可以对别人高声说话的地方;再不能通过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看富人世界的声色犬马(借以解决他的生理需要);再不能微微从他黑白的人生跳出来,接触一点彩色。
他将失去他人生的小确幸。
他怎么不留恋!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暗示了肚财并没有认为会被启文杀害——他一个流浪汉,如果预感启文将杀害他,肯定早逃之夭夭,有多远走多远,怎么可能去吃了顿面会菜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以上观点,出自肚财的视角。
关于释迦。
在我的视角,总认为释迦等于佛祖释迦牟尼。
肚财出事的那个晚上,释迦梦见和肚财见了一面,醒来,预感肚财出事了,然后他去隔壁的泳池洗了一个澡。
和这里对应的一个点应该是:启文塑的那尊佛里,藏着叶女士的尸体。
尘世的佛藏污纳垢,真正的佛预知悲苦,但也就是预知罢了。
5 ) 人道中辛苦轮回的众生
久闻《大佛普拉斯》大名,2017年金马奖大赢家,但对它的兴趣不是因为它获了奖,是因为这是为数不多和佛有关的电影,很是好奇导演会讲一个什么样的和佛有关的故事。
内地至今还没开禁,只好从优酷上看些精简版的片段,还有导演黄信尧在《一席》中的演讲,基本上情节和精彩片段也撸了个八九不离十。
万事都有个缘起,为了护国法会修建的大佛像,把影片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串在了一起,故事由此开始,佛像修建的承包人富商黄启文,为黄启文看门的保安菜埔,菜埔的朋友收废品的肚财,以及超脱的流浪汉释迦,还有和富商政商勾结的政府议员高委员,这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们上演了一出当代台湾的浮世绘。
其实影片中讲述的现实社会乱象,对观众来说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富商、政客们的灯红酒绿,酒池肉林,贫苦人民在生存线上的辛苦挣扎,劳苦奔波,甚至也不是当代社会才有的现象。
唐朝杜甫一千多年前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诗句描述了类似的景象。
可惜的是,人类社会一千多年的演化,依然没有什么长进。
芸芸众生在人道中数千年的轮回,依然逃脱不了对外在感官世界的执迷不悔,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享受还是牢牢的牵制着人类的欲望,煽动着对物质的追求,对美色的追求,对权力的追求。
不管是低层的菜埔、肚财,还是精英阶层的黄启文、高委员,在这个社会中混,追逐的都是外在的物化世界、欲望的享受,只不过低层只能通过超市的剩饭、色情刊物和偷窥来满足,而高层可以置社会伦理道德于不顾,真枪实弹的来满足那个自我。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系统中混迹,不管高层、低层,只要是执迷于外在物化世界,烦恼和空虚一样都会如影随行,大到富商黄启文对杀死情妇的恐惧,小到胆小的菜埔对老板发现他们偷看行车记录仪的担心。
你无法摆脱。
只有你真正的转向内向心灵的自我探索与寻找,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才能真正开始踏上解脱人道中辛苦轮回,了却一切烦恼的正途。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在内向心灵探索的道路上还是走得步履蹒跚,磕磕绊绊,即使佛陀几千年前就给众生指出了解脱之道,可数千年后,绝大多数众生依然在欲望的海洋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
要知道,当年的佛陀悉达多王子可是毅然决然的抛弃了一切的国家权力、财富、后宫三千佳丽,踏上了朴素的寻道开悟之路。
在他看来,生命中有比至高无上的权力,富可敌国的财富,婀娜多姿的美女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东西去追求。
另外,整个片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没有一句台词的流浪汉释迦,为什么叫释迦,我想导演是把他隐化为佛陀,默默的,静静的看着这世间的一切,和正经历着一切苦厄的众生们。
他没有深陷于这个污浊的社会,对物质有着朴素的欲望,也不需要和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拉拉扯扯,我宁愿相信他就是这整部影片中唯一的一位开悟者。
回到电影肚财死后的那句经典台词,“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的内心世界”。
其实再一次隐喻人类的自我解脱应该来源于内心世界的探索。
启文也罢,肚财也好,每一次来到人间,都是自我解脱的一次机遇,在这世间,不要再浑浑噩噩,多花些时间问问心灵,看能不能在跳出轮回的循环中迈出那么坚定的一小步。
6 ) 生活永遠是苦的,但我們可以選擇悲喜性
菜埔在肚財死後,坐在肚財家裡的“飛船”上,深刻而傷心地意識到,自己一點也不了解肚財。
在他們為肚財出殯的那天,土豆、菜埔和释迦三個人坐在路邊,土豆說了句:又沒人認識他。
菜埔立馬跳起來胖揍土豆,菜埔一定很在意這個總是“欺負”他的朋友,所以他應該真的很難過。
看到這,眼淚差不多干掉,也陷入對菜埔和肚財關係的思考,他們會成為朋友,好像根本不必要說明原因。
電影不會用幾分鐘去演他們認識或是關係變好的過程,導演也不會跳出來解釋。
可是你看,菜埔明明一點都不了解肚財,卻沒有人要去追問他們為什麼能成為朋友。
因為他們的生命裡,交朋友不是選擇出來的,就像那句對我而言略刺耳的畫外音:“社會常常在講要公平正義,但在他們的生活之中,應該是沒有這四個字,畢竟光是要捧飯碗就沒力了,哪還有力氣去講那些有的沒的。
”(如果沒有那幾個“金句”,我會更喜歡這部電影,雖然導演可能更準確解讀)和所謂公平正義一樣,“選擇朋友”也是屬於他們生活之外“有的沒有”那一部分。
菜埔和肚財根本沒有所謂的機會,像當下年輕人最愛說的,交朋友要三觀相符,氣場相合之類。
他們成為朋友,或許是因為只有他們願意跟對方成為朋友。
於是電影就順勢有了另一個金句:“現在已經是太空時代了,人們可以登上月球,卻永遠無法探索人們內心的宇宙。
”即便如此,肚財和菜埔的感情也是真實而深厚的。
他們的友情是大佛。
但他們真實的感情,也沒有辦法讓菜埔救肚財一命。
但是政-治關係可以,黃啟文和副議長之間是利益的酒肉朋友,副議長跑去派出所耍一通無賴,就讓黃啟文逃避了盤查,直接釋放。
這聽起來真的蠻讓人難過的。
大佛普拉斯沒有直接說很不公平,大家都看得見很慘。
那電影怎麼說,讓這些遭受不幸的人自己講。
就像肚財說有錢人背景很硬,問菜埔身後有什麼。
——你身後有什麼。
——香蕉,鳳梨,芭樂。
肚財和菜埔對話這一幕很有趣,非常幽默地拉近了兩個所謂社會loser和觀眾的距離,這是他們對自身社會屬性的嘲弄,看起來無意,卻引得觀影人會心一笑。
但電影裡,嘲弄本身由誰去做很重要,中階角度笑底層不行,一下搞不好就容易露出虛假的人文關懷。
所以這種描述基層人民生活的電影,賣慘是大忌。
《大佛普拉斯》最後沒有變成單純描述社會底層生活的悲劇電影,因為暗藏的幽默感機靈又討巧。
當導演說不知道肚財為什麼喜歡夾娃娃,肚財就看著鏡頭:——因為夾娃娃真的很療癒啊。
被肚財調侃騎粉色摩托的土豆說:——這電影是黑白的。
正是這些趣味讓電影層次鮮明,政權或宗教的暗喻嘲諷也通篇都是,但那些都不是我想要關注的焦點。
他們如何去生活?
生活,而不是活著。
我向來喜歡在這類電影裡找答案。
生活如此艱難(我也確信不是因為我矯情),那些比我苦得多的人,到底是如何撐下去的。
肚財生計艱難,是個收垃圾的人,但也是民間藝術家,他把色情圖片拼貼在太空艙的頂部,乍一看像西斯廷天頂,收藏的娃娃擺在家中像是個小型博物館。
菜埔關心他的阿母,他用盡一切氣力只是為了努力活著,他可能並不怕死,怕阿母沒人照顧。
他的責任感,是他老闆黃啟文那樣的“成功人士”嚴重缺失的。
釋迦聽著海潮的聲音才可以入睡,有點詩意的浪漫。
......這些細節,說不上讓角色變得如何討喜,但差異感,讓每個小角色都真實起來。
那天我走在老街上,看見沿街的店舖,賣香爐的人、修手錶的人、雜貨鋪的人,他們坐在躺椅上半瞇著眼睛,好像睡過了半生,剩下的半生也打算這麼睡過去。
他們是不是在午後瞌睡或某個下午的暑氣裡,嘆出一口氣,就從中悟出了什麼人生道理,決定就這樣活下去。
我不知道,人生思考多或少,積蓄豐厚或兩手空空,都只是一條命。
生活永遠是苦的,但電影的悲喜性可以選擇。
所以大概自己的人生也可以,用喜劇手法去演一齣悲劇。
菜埔去肚財家時,穿的那件上衣寫著:預約人間淨土。
7 ) 「有钱人的世界你看,果然是彩色的」
那代表欲望的彩色里,有一摸就湿的女大学生,有停在引擎盖前的、灯红酒绿的「紫禁城」夜总会。
肚财是捡垃圾的,菜埔在工厂做保安。
[大佛普拉斯]前段,肚财拿着快过期的咖喱饭,到警卫室找菜埔看电视,坐下来才发现电视坏了。
他嘴里噜噜苏苏,骂了句「靠北」,突然眼前一亮,要菜埔去偷老板行车记录器里的卡,回来当电视看。
这是一部黑白电影,只有行车记录器里的画面,是彩色。
肚财盯着,扬了扬下巴,说:有钱人的人生你看,果然是彩色的。
©️[大佛普拉斯],肚财将行车记录器里的记忆卡拔出来,插进电脑里,开始观看虽然,仪器拍不到车内的画面,但对菜埔和肚财而言,能听见声音,已十分可喜。
喘息声是在做爱,吮唆声是在舔「麦克风」,一句「是是是」,暴露老板见到大佬,就变龟儿子。
©️[大佛普拉斯],仪器拍不到车内的画面,但能听见车内的声音,引人遐想穷人想象富人的校园生活,催生了[小时代];想象富人的性生活,催生了[五十度灰];想象富人的日常生活,便有了[大佛普拉斯]。
当然,最后一句,是褒奖。
片中,黑白是穷,彩色是富,来回转换,将富人和穷人的世界区别开,也暗示后者对前者的向往。
这样的手法,它不是第一个。
01壹百年前,就有人這麽拍1903年,埃德温·鲍特拍了[火车大劫案]。
说两个强盗偷偷溜上火车,将乘客的钱财细软抢夺一空。
然后,跑到草原分赃,最终被警察击毙。
是黑白片,改编自美国一个真实事件。
那时,彩色电影还没出现,鲍特便以手染的方式,给某些场景上了颜色,成影史最早手染电影。
据说,这种方法需大量人力,耗时又费心,也因此,鲍特只拍了11分钟。
©️[火车大劫案],黑白画面里的部分彩色和[大佛普拉斯]不同。
到底是一百多年前的片子,说叫「色彩运用」,但完全称不上是有意识的表达,只是简单的描述存在。
所幸,1932年,「特艺彩色(Technicolor)」技术诞生。
又称特艺七彩,利用彩色滤镜、三棱镜、三卷黑白胶卷,同时纪录三原色光,再进行冲印和染色,即可用普通放映机播放。
最初应用于好莱坞拍摄。
于是,导演们纷纷放弃制作黑白片,也觉不出来,电影里若有黑白和彩色切换,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直到1939年,[绿野仙踪]上映。
女主叫桃色丝,不慎被龙卷风卷入空中,落地以后,来到一座翡翠城。
在这里,她遇到没有脑子的稻草人、缺少心脏的铁皮怪,胆小如鼠的狮子,大家携手同行,一路披荆斩棘。
©️[绿野仙踪],黑白是现实,彩色是梦境当时,彩色电影突飞猛进,席卷整个好莱坞。
[绿野仙踪]被认为具里程碑意义。
片中的黑白画面,是桃色丝的现实生活。
彩色画面,是她的梦境。
这是影史首次有意识地运用色彩。
自此,电影人开始咂摸黑白和彩色。
1945年,希区柯克拍了[爱德华大夫],全程黑白,唯结尾一抹红,像伤口呲出血。
那是一位精神病院长,拿枪对准了英格丽·褒曼的头颅,突然,又将枪口转向自己,扣动扳机。
©️[爱德华大夫],全程黑白色,只有短暂得不到一秒的红光霎时间,空中冒出红色火光,刺目得紧,是人间与地狱的界线,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惊心动魄,意味深长。
无与伦比的希区柯克时刻。
从那时起,一部电影若有黑白和彩色交织,终逃不过两个寓意,一个是时空,一个是情绪。
02世間有情緒萬種,妳是壹種何宝荣后来总是想,他和黎耀辉之间的裂痕,究竟从哪里开始的呢?
那天,他们一个卧在床上,对一盏画有伊瓜苏瀑布的台灯抽烟。
一个站在镜子前,用左手抠墙缝。
然后,抽烟的说,「黎耀辉,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刚才还明黄旖旎的世界,瞬时只剩黑白,暗示下一场离别。
不管了,就要把这黑白披在身上,纠缠,动情处,床单也在呻吟。
©️[春光乍泄],前一秒还是彩色镜头,何宝荣话音刚落,变为黑白画面后来,黑白伸到公路上去。
他们坐在车里,摊开地图,想找到灯罩上那块瀑布,可惜迷路,吵架,终于分手。
你看他们的名字,多有意思,一黎一何,可不就是离离合合。
再见面时,是探戈酒吧,黎做服务生,穿黑白西装,笑迎宾客。
然后看见何。
他被人打,嘴角泛肿。
医院走廊,黎陪他坐在长椅上,听他沉默,听他再一次说,「黎耀辉啊,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果不其然,下个镜头是彩的,打了黄光,蘸着春色。
©️[春光乍泄],两人再次和好,画面也由黑白转为明亮的彩色,带着欢欣温暖的情绪多年前,乔治的世界也是这番模样。
他和男友生活了十六年,那时酒吧初遇,沙发上对坐看书,庭院中亲吻,世界无端有柔情万种。
后来,男友车祸身亡,万种颜色尽褪,只留黑白,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是悲伤的情绪。
©️[单身男子],从前两人对坐看书,色彩柔情万种,后来世界只剩黑白但昆汀从不这样想。
黑白的罪恶之城,黄色是金钱权力、下流腌臜,红色是妓,也是暴力。
妓有一张圆床,是妖娆魅惑的红。
英雄与恶徒搏斗,流下鲜红的血。
黄色怪物奸杀、食人、满口谎言,像呕吐物和婴儿的尿布。
是罪恶的情绪。
©️[罪恶之城],黑白之城,有烈焰红唇和黄色恶人然而,在黑泽明的梦里,红与黄是希望。
他走在梵高的画里,放眼皆是黑白,了无生趣,抬头一个硕大的太阳,是梵高孤苦寂寥的心里,裹住的沉甸甸的热。
于是,他情不自禁摘下帽子,像信件末尾的「此致、敬礼」。
©️[梦],周遭都是黑白风景,抬头竟是硕大的红日最难忘的,是那只骚哄哄的黑天使。
她本已嫁为人妇,却在那事上得不到满足,压抑到洞底时,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位纳粹军官。
黑白,是被浇熄的火。
彩色,是重新燃起的欲。
©️[黑天使],色彩随着女主的情欲而变烧到极点时,她渴得不像话,心甘情愿被军官按下头颅,埋在他两腿之间,长长短短,近了又远。
03時空如亙古長夜,妳是破曉那年初秋,太阳张贴在瓦蓝的天空。
一挂马车从山路上跑来,套了两匹红马,一匹铁灰,斑斓,拖出一排辙印,敲打着进了三合屯。
好多人都聚在屯头,说是接先生。
招娣也在,特意穿了红布衫,看见先生宽肩长腿的,纵身一跃就跳下马车。
对视时,他目光清澈,她心头一热。
他们结合生子,她织布,他教书。
多年以后,他成了糟老头,死了,心脏病,还赶上一场鹅毛大雪。
©️[我的父亲母亲],彩色和黑白是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瓦蓝的天,红色的马,是过去了。
黑白的炕,黑白的脸,才是此刻。
彩色与黑白,是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
就像马小军的青春。
打架、拍婆子、溜门撬锁,肚里憋着坏,是被荷尔蒙裹住的少年。
二十年后,人到中年,满世界都是黑白。
他和朋友坐在白色的凯迪拉克里,喝酒碰杯,缓缓驶过长安街。
彩色与黑白,对应青春与中年。
世异时移,他终生再没可能寻回青春的幼稚与无知。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阳光灿烂」四个字。
©️[阳光灿烂的日子],彩色和黑白是青春和成年两个时空辛德勒一直忘不了那个红衣女孩。
克拉夫正在屠城,他站在山头,视野里都是黑和白,直到看见那一身红。
不显眼的,却是影史最刺目的,独立于战火之外,和身后的难民与军官隔开,分明属于和平年代。
©️[辛德勒的名单],黑白人群中的红衣女孩还有那位患了色盲的少年。
失色的城市于他而言,不过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他看不见斗鱼身上鲜活明亮的颜色,那和城市一样,在他的世界之外。
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调低这黑白电视的音量,然后,开着机车到处走,不回头。
©️[斗鱼],鱼身那么艳丽,甚至有些刺眼,可惜少年看不见除此,便是[碧海蓝天]里的黑白回忆,[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彩色的比利。
[超脱]里黑白色的过去,[巴黎战火]中的彩色新巴黎。
还有[大佛普拉斯]。
肚财和菜埔透过行车记录器,听见了老板狗屁倒灶的风流事。
那代表欲望的彩色里,有一摸就湿的女大学生,有停在引擎盖前的、灯红酒绿的「紫禁城」夜总会。
有钱人的世界你看,果然是彩色的。
©️[大佛普拉斯],肚财和菜埔在黑白世界里,看着行车记录器里的彩色光影黑白与彩色,是新旧、贫富,过去和现在,梦境与真实。
但无论如何,总有一边,是另一边的心之所向。
总有一边,觉得自己穷尽一生都是亘古长夜,望见对岸,才算破晓。
-作者/六姨太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8 ) 大佛眼中的人间是什么颜色
(文/杨时旸)溽热又粘腻的夏天,人们步伐懈怠,在荒草、土坡和低矮的厂房里混生活,台南底层世界的随意一瞥之中,《大佛普拉斯》的故事徐徐展开。
戏谑、敷衍又总想表演真情实感的送葬队歪斜排成一队,吹奏着荒腔走板的《友谊地久天长》,这几乎奠定了电影的基调——一种不加修饰的、怪诞却真切的现实,包含着重压、无聊,失却方向却又只能苟且的生活窘境。
很难说清《大佛普拉斯》的色调——当然,这是指它精神意义上的“色调”,它时而嘲讽,时而喟叹,更多时刻不动声色只负责呈现,而它的影像是黑白的,但又不全是,90%关于底层世界的叙述中都用黑白呈现,有时像粗糙目击,而有时像淡墨点染,而其余10%的上层世界的图景又都是彩色的,霓虹灯和广告牌璀璨又俗艳。
这浅白寓意谁都能分辨得出,穷困生活斑驳晦暗,富有人生声色犬马。
仔细区分,凡是客观讲述故事的桥段,一概都是黑白色调,包括那些名流一众人在泳池里狂欢的时刻,而通过其中角色的眼睛望出去的世界,才是彩色的,而那些时刻都是通过行车记录仪的视界呈现的,是的,这是电影中另一个有趣的视角——有关偷窥以及对偷窥的偷窥——前者是局中人所做的事,而后者是我们作为观众所做的事,银幕内外完成了一次有趣的互动。
那行车记录仪的画面只呈现路边、街角和桥下的无聊世相,画外音却是车内活色生香或云波诡谲的对话,彼此对撞出更浓烈的悬疑、刺激和窥伺的快感。
《大佛普拉斯》看起来是个轻巧的小品,导演并不想故作沉郁,他自己从开头就用松垮的声音絮叨着,一会儿和观众说说这部电影谁是制片,谁又是导演,一会儿又提醒一句,自己会时不时在故事中途窜出来解读一下剧情,让大家做好准备。
这是一种标准的文艺理念的实践,打破观众对故事戏剧性的沉溺,实现某种间离效果。
有一种理论认为,营造一种笼罩一切的、让观众信以为真的虚构真实,观众一直沉陷其中,是低级的观看,而时刻有能力跳脱出来,清醒审视、旁观才是高级的观看。
《大佛普拉斯》对这些游刃有余,有能力随时拉拽观众出戏,又能旋即把观众扔回故事现场。
那么,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菜脯和肚财,底层打工仔和拾荒者,在生活的最下层疲于奔命,最大的乐趣不过是吃着冷掉的便当偷偷窥伺老板行车记录仪中的景象和车内的对话,本想意淫一下其中的咸腥,听听姑娘的娇喘和老板的调笑,但没成想却意外撞破一桩杀戮。
老板开的工厂承接了一尊佛像的制作工程,巍峨的大佛庄严地观看一切发生,又意外地被血色玷污。
这就是全部了。
有人说,这故事是揭露是讽刺,确实,它有着锋利的刃和尖锐的刺,不动声色地掠过一切看起来身居高位和煞有介事的人,呈现背后的不堪与肮脏,但它绝不是一部较劲于此的电影,它的表情并不凌厉狰狞,竟然如此松弛,那些揭露的时刻不过像是偶然撞见,瞟上一眼,嘲讽一声,牢骚几句,然后仍然归于平淡,就像在那间屋顶漏雨,空调失灵的收发室里,菜脯和肚财平淡说起,“落土八分命”,老板能叫Kevin,而自己只能叫肚财,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争不来的。
导演批判所有虚妄、虚伪和虚假,并不想成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分子怒目圆睁拔刀相向的样子,他更愿意还魂和降落到和肚财与菜脯一样的维度和低处,悲悯地看看周遭。
导演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那些象征、隐喻和涵盖着各种指涉的逗趣随处可见,肚财抓来的满屋娃娃,居住的“飞碟”,终日惶惶的菜脯穿的背心上印着“人间净土”……这些细节密布各处但又内敛隐藏,毫无刻意。
大佛普拉斯,就是大佛plus,戏谑的名字却也意外地意涵丰沛,一部短片扩展而来的电影,一次偷窥引发的连锁反应,衍射出的事态与万象,大佛+,加什么呢?
大佛低眉慈悲,不动如山,最终却被人当做盛装罪恶的容器。
+后面跟着的或许应该是周遭与全世界,以及我们无法参透的人心,只是,从佛的眼中望下去,看世间百态,看人间众生,到底该是灰白还是彩色?
9 ) 如果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名称,我会将它归类为:操蛋片
一某些影评人喜欢说“港片已死”,更喜欢说“台片必死”。
但《大佛普拉斯》的存在,似乎是在宣告:台湾电影生机勃勃。
不但生机勃勃,还制造了2017年华语电影的最大惊喜。
“惊喜”比“喜”多了一个“惊”字。
多出的是意外。
《大佛普拉斯》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妙处。
导演拍法妙。
我们见过太多有旁白的电影。
旁白要么是主人公,要么是主人公的亲人或者朋友。
总之,旁白是一个视角,但这个视角依然来自影片里的故事。
《大佛普拉斯》不同。
本片的旁白是导演自己。
影片中旁白的身份,就是导演。
他在正片开始前就告诉观众:我会不时出现唠叨两句。
在故事进行中,导演会突然以旁白的方式出现,介绍影片中配乐使用的来由。
本片中的角色也会和观众有所交流。
男主喜欢抓娃娃,他会突然对着镜头说:夹娃娃很疗(治)愈。
这还不算特别。
影片中有这么一个桥段:男主和朋友在公路上骑车,朋友骑着个粉红色的摩托车。
男主说:男人骑什么粉红色的摩托车。
朋友说:这是个黑白片啊。
话音刚落,本是黑白色调的电影画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抹粉色。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以为《大佛普拉斯》是部喜剧片。
二如果能让人发笑的电影就是喜剧片,那《大佛普拉斯》可以算是。
它太有趣了。
那些足够让观众反复玩味的小细节,怎么看怎么好笑。
而且是很高级的幽默。
但如果一部电影必须得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才能被定义为喜剧片,那它则大相径庭。
我也不愿意说这是部悲剧片。
如果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名称,我会将《大佛普拉斯》归类为:操蛋片。
它处处流露出魔幻色彩,却又无比真切地描摹着现实生活。
而现实生活,实在是太他娘的操蛋了。
原谅我又粗俗了。
我在文章里写脏话,是为了和电影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角色离得更近。
而我做出上面的解释,是为了再次强调影片中导演的叙述手法。
在我解释我为什么会写脏话的时候,我和在电影中间突然化身旁白的导演做了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对戏剧有所理解,会知道英国人演莎翁戏喜欢这么玩。
哈姆雷特会对着观众说出大段独白。
观众也并不会觉得太过突兀。
如果你对戏剧了解得再深一点,你会知道导演的叙事手法多半是受到了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理论”的影响。
简单地说就是:让观众看戏,但不入戏。
我要说句玄之又玄的话:不入戏,才是最深的入戏。
当导演不断用旁白制造出“间离效果”让观众出戏的时候,观众变成了真正的旁观者。
看悬疑片,观众会把自己想象成侦探。
看动作片,观众会把自己想象成英雄。
看AV,观众……看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呢?
越是真实的人生,越没有“感同身受”。
与其无法真正靠近,不如悄然远离。
我们在导演的引导下得以观察起影片中几个小人物的人生。
却突然发现:我们和这些人隔着的,不只是导演的旁白,不只是电脑屏幕,更是一片浩瀚的宇宙。
三《大佛普拉斯》的主角叫肚财。
他是个拾荒者。
操,说得太书面了。
他靠收破烂为生。
他有几个朋友。
一个叫菜埔。
“菜埔”在闽南语里是“萝卜干”的意思。
菜埔家有老母,给文创公司老板黄启文看大门。
肚财还有一个朋友叫土豆。
开便利店,骑粉色摩托。
土豆、菜埔和肚财一样,都是小人物。
他还有个朋友叫释迦,在片中只说了一句台词:我就四处逛逛。
不知道佛祖自己是不是整天也就四处逛逛。
说回菜埔。
肚财喜欢去菜埔的门房闲聊。
在愚钝无知的菜埔面前,肚财才能勉强找到一点自信。
无聊的两个人想到拿菜埔老板黄启文的行车记录仪来看,没想到一看之下看出了麻烦。
起初,有淫音入耳,两人分外激动。
看得多了,两人竟看到了黄启文行凶杀人的经过。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命运也就发生了改变。
买不起酒喝的肚财死于了醉驾。
没有人知道真相。
也许除了黄启文。
和肚财他们不同,黄启文开着奔驰,勾结着政府官员,勾搭着形形色色的女人。
在肚财和菜埔翻看旧色情杂志的时候,黄启文正和官员们纵情声色。
但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肚财没有财,烦恼就是财。
黄启文有财,但他也担心丢掉财。
因为他有了新欢,他之前的情妇便用他的秘密威胁他问他要钱。
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安全的时候,他杀了人。
肚财和菜埔不会知道黄启文的内心活动。
就像黄启文不清楚肚财和菜埔的生活一样。
四底层小人物和有钱人的生活也是被“间离”开的。
用影片里的话说:有钱人的生活是彩色的。
至少在底层小人物的眼里。
毕竟他们的生活是黑白色调的。
对于肚财来说,欲望就是黏腻的二手色情杂志,生存则是挂在嘴边的“干”。
他会恐惧、会兴奋、会悲伤,但却不会想象。
肚财是不会迷茫的,因为他不知道迷茫是什么。
每天重复的生活,让他不满,却不会不安。
因为他知道: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
只要晚会上才唱《爱拼才会赢》。
肚财不会作弊,也没有背景,所以他知道自己一辈子也不会成为有钱人。
菜埔也一样。
如果不是在好奇心驱使下偷看了黄启文的行车记录仪,肚财不会和黄启文有任何交集。
哪怕是面对面对视,黄启文的视线里也不会有肚财。
黄启文的生活里则充满不安。
他白天为政府造着大佛(Buddha),晚上在隧道里玩着puta(西语“贱人、妓女”)。
为了大佛,他费劲心机;因为情妇,他铤而走险。
妓女和大佛相似的读音,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哪有阿弥陀佛么么哒,世间全是阿弥陀佛啪啪啪。
影片的最后一幕,大佛被无数僧侣供奉。
一片祥和。
突然,大佛响了。
看了电影的观众知道,黄启文把情妇“杀死”后放进了大佛里。
那么,这声响是否意味着情妇没死呢?
这其实不重要了。
最肮脏最隐秘的,和最神圣最庄严的,组成了那人间。
最富贵最复杂的,和最贫穷最简单的,构成了这生活。
导演黄信尧曾这样解释影片结尾大佛的声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叶女士(启文情妇),我们都被封在大佛腹中,那一声声撞击,不就是我们自己发出的吗?
是不是有些发冷?
操蛋片突然成了恐怖片。
孤独的你我,终于体会到了极致的惊悚。
这也是一种“间离”。
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无法接近的恐慌感。
影片里有这样的金句:“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永远,是种定数。
在定数中,却也有诸多不定。
正如林生祥为本片创作的主题曲《有无》里的歌词:人生无定着,世事歹按算。
看不透的,就别看了。
10 ) 短評太短只好寫在這邊,卻不小心越寫越多
記得大佛普拉斯當初上映的時候有和台灣彩券合作,可以用沒中獎的彩券去換購電影票,現在想起來也是諷刺十足阿!我是今天在電視上看的。
大佛普拉斯是Catchplay除夕夜的選片,幸好當時沒看!大過年闔家看這題材電影太尷尬了。
但拍得蠻好看的,特別推薦,我覺得影片本身就是個評論,再多的評論都搔不到癢處,頂多就是錦上添花。
因此我對本片不做任何評論,只想抒發我的經驗身為當地人,總心有戚戚焉,尤其是聽到海口腔的台語,整部影片呈現的就是那種和我同個空間但卻與我完全不同的世界,也不太可能進得去的世界。
是那種開車會經過-會開很快經過,但不太可能停下來看一眼的世界.....(對就是隧道內的通道)那是一個會無意識忽略與潛意識嫌棄的世界,我一直知道有那個角落,卻視而不見。
大佛普拉斯真實重現,沒有加油添醋,沒有故作可憐。
就拿一開始的場景來說吧!菜埔的媽媽去打點滴的七股衛生所,七股這個地方在我印象中就是小時候去吃便宜海鮮的地方,開車半小時就會抵達,感覺就是富裕的小漁村,雖說沿途總會經過一些破敗的地區,小時後總會想,誰會住裡面阿?但也就儘限如此,車子就直接進入海鮮餐廳,吃飽後在車上睡著,下車是被家人叫醒的。
後來大一點去七股海邊寫生,替黑面琵鷺做活動,沿途有些像肚財或釋迦那種奇怪的人徘徊或是過來圍觀,我們會害怕會遠離,但久而久之就習慣了,知道他們存在但不會去細想他們的事情。
說到衛生所就又更不明白了,知道有這種地方,但從來沒去過,一直以為衛生所只是存在極度偏遠地區,或許是個該考慮淘汰的公立機構,生病不是就要去大醫院嗎?而且七股並不落後附近也有一些中型醫院(七股是台南市區的一部分,當然這很可能是某種荒唐的政治結果)。
但我錯了! 還真的有需要,就如同我不習慣進去他們的世界,同樣的她們也不一定知道該如何進去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
不少議員也就那樣,是真心讓人瞧不起,但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當選的,大概是什麼樣的選民選出成什麼樣的政治人物吧?!怪誰呢?紙風車的美國(美國,是李永豐真實世界的綽號,先有綽號才有《一一》電影,裡面那個朋友美國就是他)所扮演的副議長,真實將地方政治人物的生態表露無遺,(一般所知的回扣大概是拿一成,這個拿三成.....好像有點多,但不誇張,畢竟是副議長阿)還有那種浮誇低級的泳池音樂派對,我還真有見過,但那是小時候去暴發戶家裡會有的場景,至於他們現在品味有沒有提升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宗教部分也是滿滿的寫實諷刺,在我看來根本是雜揉了X濟和佛X山元素在裡頭,這種我佛慈悲的事情大過年就不批評了。
當然還有好多細節,可能要某些經驗才有感觸,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能看得開心有所收穫才是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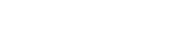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开篇即立的解说旁白,作为强烈的形式之物,竟能有助于本身已经很丰富的剧情去上升到某种哲学思考高度,当然这也得益于导演的刻意引导,让观众既脱离故事重获上帝视角,又跟随小人物命运沉浸剧情。行车记录仪的妙用,更是把这番沉浸把玩出了窥视传递的乐趣,员工看偷情,我们看悬疑,而最终一起置身大佛
又是一部替穷男呐喊阶级压迫的片子。穷是黑白,富是彩色,穷无女人,富有美女,穷不敢言,富草菅人命。唯一的新元素是把用佛像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具象化了,安详与威严背后,禁闭着呐喊。如果以真正的最底层——穷女来拍一部片子,大概处处是压迫与煎熬,而非仅仅是坐在保安室吃盒饭看黄片的贫困了。可以试想一下拾荒女,流浪女,能活得像他们一样自在吗?
现实主义的尽头是魔幻。让我到你肚子里看一看
生而平等是不存在的,死而平等也是不存在的,唯有人类永生的孤独是众生平等的。
惺惺作态的,我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远离的那种电影
佛祖:荒谬
满怀希望去看的,但对女性的歧视和“物化”真的太过分。从头到尾都在欺压和消费女性。
架构一场戏内戏外的双重偷窥癖,闽南语局限了笑点
魔幻又荒诞,是Buddha还是Puta,片名的“大佛”就是最大的讽刺。皮囊之下皆有秘密,佛像里藏着死尸,捡废品的大叔房间藏着装满了布娃娃的飞船。世界不仁,社会不义,法律无公正,警察无正义,有钱人的人生,果然是彩色的。只剩我们这些蝼蚁相互倾轧,摸爬滚打,苟且偷生,连捧饭碗都要用尽全力,哪还有力气想什么公平正义。看,连他们的名字,肚脐,菜脯,都这么不起眼。“等我有钱了,我也要取个英文名。”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妖魔鬼怪,这世界真是从根上烂透了,烂到底了。
不黑不色不幽不默。
有头没尾,或者说那个诈尸般的结尾矫情过头了。就算有钱人的人生才是彩色的,也没必要拍个黑白电影,还不如看行车记录仪呢。这个和《不能没有你》一样,除了把电影强行弄成黑白的,就没其他办法表现底层小人物的凄凉生活了?这电影我最喜欢的一点是,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一部完全被高估的作品。当小聪明变得泛滥,那么它就是影响作品本身的负面因素。大量的导演阐述旁白破坏了电影本身的视听语言,对于故事细节与情绪的建立一股脑的通过旁白来表达,太掉价。
很聪明,也很古怪。堆砌了很多直接的信息(非符号),没有画外音会显得很刻意,但导演自己跳出来讲,声音又饱含真诚,这种刻意便被部分消解了。但也因此,影像原本可能具有的强力(震惊、唏嘘…)由于画外音这种非常文学化的介入导致电影最终变为一份观看与阅读的文本。处女作鼓励,不会看第二遍。
切入点蛮有趣,以小窥大。佛度众生?不存在的。★★★☆
◎法国文化中心·野草莓放映计划
不喜欢这种颠覆
佛陀低眉,是不忍视,那些日夜上演在他眼皮底下的人间乱象。导演自带吐槽模式,是蛮有意思的想法,但旁白过满,过于热衷帮观众划重点,掌握中心思想,填塞了影像之余的每一寸空间,恨不能交待得巨细无遗,就欠了思索和回味的余地。你不妨在信息上啰嗦,但不能在意思上点透。从聪明到匠气就这点差别。
形式笨拙,内容空洞刻板,剧作、调度、技术还不如《血观音》。
不能认同的偏激角度。
镜头语言很不错,许多中景镜头只拍了人物肩膀以上的部分,并在景框上方留白,非常耐人寻味。评论音轨和旁白二合一的手法还是第一次见到,充满了实验色彩。去掉旁白观看,情节完整,但节奏发生变化,叙事上有大量留白,摄影充满隐喻。去掉画面只听声音,竟然是一部完整的有声小说。导演真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