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剧情介绍
《妈妈!》长篇影评
1 ) 半首诗
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天。
春天是你的生命,秋天是我的生命。
你那绯红的面孔,像春天盛开的玫瑰,我这疲倦的眼睛,像秋日暗淡的光辉。
////////////////////////////////////////我应该向前一步,再迈一步向前,那时我就跨上了,冬季冰冷的门槛。
假如我后退一步,你再迈一步向前,我们就一起跨进,美丽而炎热的夏天。
同时考虑历史背景和审查制度才能在院线*看懂*这部电影。
裴多菲的诗一首,影片中读了前半首,也拍了前半首。
朗读前半首的镜头是过分文学化的又过分显明的隐喻——母亲被指派为春,而女儿被指派为秋,影片在表面上自此开始了对于春—秋身份倒逆的讲述。
而未读出的半首里,周夏被指派为夏,也许父亲被指派为冬。
我以为周夏的戏份——通俗地说——是在为过审而大摆其烂。
从红发到黑发标志着性情由“非主流”到“正统”;被请客时说出根本不符身份的台词;回来探访恩人突然开始与上下文完全割裂的歌舞桥段……不敢相信哪个神智正常的导演会在2022年这样处理。
“美丽而炎热的夏天”的幻景或许沦为了审核制度的牺牲品,彻底被涂抹成了阳光沙滩的加州风情画。
冬天则被掩盖了,它隐而不显,只在春和秋的对话中以碎片形式一点点浮现。
冯济真在床上的忏悔中吐露:她当时退了一步,在还是春天时退了一步——于是永远落入了冬天。
我们完全可以以同时代的哪个故事来补全冬天的故事,在漫长的严寒里,个个悲剧都面貌相似。
春和秋的故事,即《妈妈!
》的标题所涵盖的故事,是诗化的。
但春和秋毕竟只是两个季节,只面对两种际遇,所以只有“半首诗”。
半首诗聚焦的知识分子母女作为女性和市民具有尽可能好、尽可能体面的处境,以至于其对话在粗粝的世俗间显得不真实。
她们试图清醒而自觉地对抗病症,以种种优雅的布景负隅顽抗,试图在注定失败的反抗过程中维持良好自足的生活。
观众在这个层面上可以领略到古典式的悲剧意味:冯济真在清醒时为自己做的形同后事的准备在病中纷纷宣告无效,四处贴起的纸条挡不住她将房屋幻想成各种他处、整得纷乱不堪;当初平静地说出可能将妈妈视作姐姐,可是最终竟将妈妈视作了别人的妈妈,更添一番可悲。
剩下半首诗——关于夏天和缺席的冬天的诗——毋宁说是反诗学的。
关于母女高知身份最清晰的符号表述来自于影片开头读诗的桥段。
痴迷旧版简装书,讲究译本,对于文字和阅读的老派热爱被清楚呈现。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文字在之后的剧情里逐渐崩坏。
冯济真撕毁父亲日记——作为治疗病症的道具“出版”日记——冯济真失去读写能力,三个阶段里,文字/诗越发缺席,越发缺乏维持体面生活的力量。
三个阶段也许对应冯济真意识深处回避过往之罪——母亲不论因何原因成为女儿遮掩过往的共谋——无力遮掩过往,将要开始最后的遗忘和忏悔。
这三个阶段绝无知识分子的体面可言,与尽可能维持诗意的负隅顽抗也毫不沾边,它只是冷冰冰的历史斥责。
影片在结尾处回到了海的意象,纵观全片,海并非是一个和阳光/沙滩……并置的,因而可以定义的词语。
海也是冬季的,浪潮阴沉,水色晦暗。
它像前面出现的众多水面一般制造着幻觉,但它的幻觉更大、更终极,需要整个人投身才能领略。
冯济真在梦魇中打捞着父亲的遗稿,这是诗。
当她在失忆中说出了过往的罪孽,当母女历经几十年的忏悔和清洗,换上正装,一身清白地步入大海,和投湖的父亲会面,她们绝不会是优雅的。
记得突兀地插入的那些纪录片式的水下镜头吗?
她们会在那种混沌蒙昧中作动物性的挣扎,然后死去,就像父亲的命运。
2 ) 书面表达为什么不会成为问题?
问题不在于电影台词是用书面化的语言写成。
由此便指责“不说人话”,得为导演喊一声冤。
因为这句批评暗中隐含了一种约定俗成实则走入误区的观点:电影应该是对现实的如实反映。
这样也就要求电影里的角色其言其行需得符合现实世界的约束。
“不说人话”的指责便由此而来,一旦角色讲起过度文学化的书面语言,普通观众便招架不住了。
事实上,没有哪条规矩事先定下电影要符合现实。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自古有之,或许因此才让这种观念变成教条。
尤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入这片大地后,教条甚至变成了颠簸不破的真理,让创作者和观众都深受其害。
如果电影仅仅反映现实,那么电影还有存在必要吗?
我们只要在现实世界里多看多体验就行了,作为副本的电影失去观看价值。
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创作理念,为呈现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可以采用其他创作理念,动用其他创作技巧。
不然所谓的浪漫、荒诞、魔幻、超现实等等就没有其存在意义了。
正是有后面这些手段,对现实主义做了补充,我们才能创造出远比现实世界更加精彩、更加迷人的艺术世界。
在其中,我们获得意外的体验,从而对现实产生进一步的认知。
《妈妈!
》的台词确实是过度文学化的,它更加适合一个虚拟的舞台,而不是真实的世界。
但因为这部电影刻画一个有着知识分子背景的家庭:考古学家、物理教师等,人物日常也多浸染文艺作品,养成书面化的表达习惯,似乎也能理解。
就像民国时代现代文学作品或当时的电影作品,文辞也多留有古文的韵味,并非完全彻底的日常白话口语表达。
另外,电影的重心也没有放在对现实肌理的还原上。
母亲与女儿之间,更加像文学作品里可能出现的人物,通过反转母女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来探讨女性间的亲情。
我们甚至很难发现故事背景在杭州,空间环境被抽离了,单独凸出的住宅像一个舞台,两位角色在其上展开“相爱相杀”的情感戏码。
《妈妈!
》更偏向戏剧,反日常的对白并不特别显得尴尬。
当然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饰演母女俩的是两位经验老道、演技精湛的资深演员。
即便在台词过度书面化的情况下,她们也能很好地控制不让念白往朗诵的方向发展。
不然的话,确乎就变成类似戏剧舞台上为念台词而念台词的表演了,失去生活的味道。
如若换成其他一般的演员,这部电影很大可能要崩坏。
导演实在应该感谢这两位出色的女演员。
3 ) 母亲的慰藉
我早有预料这电影对我来说会是催泪弹,所以我一直不太想去看,今天下午天气好,想着就把它看了,一看果不其然。
而关于母女关系的描绘,跟导演上一部的《春潮》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春潮中母女关系中的控制、反抗、互相伤害,在这部电影里都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牵绊,安慰和互相治愈。
而且相对于春潮那略显生猛的讲述方式,这部电影更唯美和温和。
在电影中女儿年轻时犯了错,她没有原谅自己,甚至在患上阿兹海默症后,那些压抑欲望、用来惩罚自己的、已经过了大半辈子的生活方式已经忘记,但是她依然无法忘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母亲都看在眼里,但是她知道不能说也不能劝。
有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给父亲开门导致父亲自杀的人不都的活得好好的的吗?
但是我相信道德感高的女性,会放大自己的无心之失,而同样明事理的母亲也知道,这本不是孩子的错,而且只要孩子需要自己,母亲在任何时刻都会挺身而出,哪怕已经85岁的高龄。
只要相信这一点,就一定会为这部电影喝彩。
4 ) 看不懂《妈妈!》是因为电影要讲的其实是《我们仨》
其实很多人关心的是,《妈妈!
》会不会很好哭?
我的答案是,很好哭,妈妈题材结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题材确实容易让大多数人产生共鸣,因为上了年纪的长辈,确实健忘,有时连一些特别亲近的人都认不得了。
生活中更多称为:糊涂了。
电影中妈妈和女儿的相依为命,最好看最催泪的在于照顾身份的反转,本来事无巨细照顾着妈妈的女儿,突然因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时隔多年再次成为了被照顾的对象。
这种85岁妈妈照顾65岁女儿的戏码,辅以类似妈妈本是头孤勇的母狼的台词,一下让妈妈的感人形象呼之欲出。
向吴彦姝、奚美娟老师致敬,感谢她们的精湛演出。
电影《妈妈!
》本来该是杨荔钠三部曲:《春梦》、《春潮》、《春歌》中的第三部《春歌》,所谓歌,指的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虽然从《春歌》更名为《妈妈!
》,强调妈妈才是电影中当仁不让的主角,但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奚美娟扮演的女儿得病后连妈妈都不认识了,却依然记得爸爸?
吴彦姝饰演的妈妈,八十多岁高龄能劈叉、能爬高蹦低,思路清晰、过目不忘,动不动还要来罐雪花勇闯天涯,会撒娇求暖床,会吐槽说要被洁癖女儿洗成秃毛鸡,家里遭贼第一反应是,先看看自己鞋盒里藏匿的小金库是否安然无恙。
就是这样高寿健康、聪慧高知的顽童形象,让我想到了杨绛先生,钱钟书先生早逝,在她的回忆录《我们仨》中,女儿最后的日子是她陪伴着一起度过的。
再想想电影中的爸爸形象,还真的颇有几分像钱钟书先生。
当然,剧中的人物是虚构的。
根据电影中的剧情,女儿疯疯癫癫地回到自己年幼时居住的旧宅,只见老屋内,昏黄的灯光晕染开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跳舞。
毫无疑问,这是女儿心底最幸福的时光。
手指过蜡烛火苗的行为,和打响指代表我爱你的暗号,证明他们曾经是幸福的一家三口,直到爸爸去世,这个家开始变得破碎。
只剩下妈妈和女儿相依为命。
片中有个镜头,一对游客父女路过一处被保护起来的古桥通利桥,父亲一时想不起另一处古桥的名字,是奚美娟饰演的女儿告诉他们,那座叫女儿桥。
而当那对年轻父女走后,她拿着花在桥旁暗自神伤,有几分怀念,几分感伤,还有几分无人诉说的忏悔,而那天,正是她父亲的忌日。
根据电影中母女的对话可知,爸爸是因为女儿的一些不可描述的行为导致投湖的,所以女儿会有大量与水有关的镜头,泛舟的镜头,无疑是在表达一种哀思。
而且在电影结尾,旁白又说,妈妈是大海,我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爸爸是不会游泳的鲸鱼。
结合爸爸投湖的行为可知是溺亡。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拍摄母女二人的镜头是从海里拍摄的,随着海水波浪,主观的镜头时不时被海水完全遮挡。
这完全就是溺亡的爸爸的主观视角镜头啊,让人细思极恐。
女儿年轻时是对不起爸爸的,所以她长大之后,一旦有时间,就会拼命地做义工去帮助别人,企图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宽恕。
这也是为什么,当文淇饰演的问题少年出现时,先是公交车上栽赃,然后是入室作案,但她始终没有愤怒与怨恨。
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这犯了错的女孩子(也包括曾经的她自己)都是可以被原谅,可以走上正轨好好做人的。
在公交车上女儿眩晕的那一幕,是否又是父亲当年所有过的遭遇?
所以当我们心中疑惑,她为什么要给文淇饰演的问题少女钱的时候,问题少女说,我们不一定是谁拯救了谁呢。
再后来,问题少女带着自己的孩子投奔二老,更是一种美好的寄托。
因为作为女儿,未婚的她是没有孩子的。
问题少女所带来的孩子,其实是弥补了女儿心里的缺失,甚至可以说,她是女儿得到救赎的化身。
而阿尔兹海默症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老年痴呆症,它包含着一丝对历史既往的遗忘。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对过往的释怀,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对历史的健忘。
究竟是什么不重要,它终究要被遗忘,而我们需要珍惜的,是当下的相濡以沫。
5 ) 这部中秋档,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中秋档即将在本周正式拉开帷幕,只要稍微留意下排期,就会注意到今年的中秋档也许是近3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光院线片就多达10余部之多,其中不乏像李少红、尔冬升这样的名导在列。
杨荔钠相对低调很多,她的新片《春歌》(现更名为《妈妈!
》)选择“错峰出行”,于次日公映。
作为“女性三部曲”的收官作,受疫情影响带来的跳票以及随后的更名,让人一时无法得知片方决定换名的真实动机。
也许是为了照顾市场,导演和片方想用更贴合大众情感的名字助力票房。
但比起片中呈现的母爱,《春歌》似乎更能反映这部作品的本质,也和导演过去两部作品中一再提到的“春”一脉相承。
虽然三部曲中的原始片名都有一个“春”字,但它们所指代的含义却是截然不同的。
《春梦》讲述了一段失去激情的婚姻,其中,“春”指代的是妻子的性幻想——多年的寡淡,已让她和丈夫的亲密关系逐渐疏远。
而到了《春潮》,“春”则被拿来指代一段降至冰点关系的解封。
考虑到女主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决裂,这种解封应该指的是她和女儿之间的和解,和一种新型亲子关系的建立与复苏。
《春歌》某种意义上重合了前作的话题,因为二者都提到了母女关系,只不过修复顺序从前作的女儿身上转移到了本作年迈的母亲身上。
因罹患阿兹海默症,在大学任教过的女儿性情大变,开始频繁失忆。
原本看似悲剧性的病魔,却意外带来母女间的谅解,而谅解的背后,一段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不光在主题上和《春潮》接近,细节上也能看出它和《春梦》之间的互文。
在表现女儿病况时,导演非常喜欢利用水的意象来强调角色主观意识的模糊和丢失。
水的状态也在随主角病情的加重而发生改变(比如公车上,导演采用线条状波纹来暗示主角可能产生的幻听和幻视)。
如果这个意象还只是对角色初期病情的模拟,那到后来的情景再现,则直接挑明了角色的病情已经恶化。
镜头在重现角色脑海中的影像时,多次将视点落在其早已过世的父亲身上。
对于父亲的离世,女儿一直心怀歉疚,在她的内心深处,其实相当崇拜才华横溢的父亲。
影片用一个非常暧昧的幻视镜头来表达这样的崇拜:已经陷入阿兹海默中期的女儿在和母亲追忆童年往事时,忽然身披母亲结婚时用过的婚纱,前往儿时寓所,在那里重温和父亲相伴的岁月。
之所以说这个场景充满暧昧,是因为观众不但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对逝去父亲的眷恋;婚纱的出现,还暗示着女儿的恋父情结——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年至迟暮仍未嫁人。
到这里,“春”的意象再一次被以非常隐晦的方式注入进来。
旁人无法理解,如此优秀的高校教师怎么会找不到与之契合的另一半,但其实,除了上述暧昧场景,影片已经用多个细节交代了人物的行为逻辑。
比如,女儿大部分时间喜欢戴手套出门,这一方面是源自于她需要整理父亲的考古材料,必须时刻保持手部的清洁卫生;另一方面,从母亲抱怨她经常给自己洗脸的角度看,这同时也说明女儿的自律和爱干净。
加上高级知识分子背景,一般的凡夫俗子恐难入其慧眼,何况她的童年还有一个如此优秀的父亲作为榜样。
当然,为了避免观众过度解读,导演还抛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线索去帮助大家理解女儿的终生未婚,考虑到其触及话题的敏感性,影片在这方面刻意“语焉不详”,但对老观众来说,大致意思已经能猜透几分。
经由母女的对话,一段从未公开过的黑历史跃然而出。
原来,父亲当初的死和女儿的见死不救有相,为了赎罪,女儿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决定等父亲回来后再解决个人问题。
但显然,随着父亲投湖自尽,这一切已然化为泡影。
影片虽然没有深究历史事件对女儿的影响,但只要熟悉那段岁月的人,结合她较真的性格,应该都能理解人物的动机。
如果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可以再去找来张艺谋的《归来》重温,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通过这样隐晦的表达,导演杨荔钠显然是想借宏观的事件,来表达个体在经历的时代创伤,且这种创伤即便在多年后依然具有相当的破坏力。
具体体现在:发病前,女儿为了压抑自己的负罪感,刻意疏远了和母亲的关系;发病后,女儿的坦白又对貌似已从创伤中走出来的母亲造成了二度打击。
那么到底在歌颂什么呢?
毫无疑问,对象当然是母亲,通过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导演歌颂的是母亲无私又无畏的爱。
诚如老母亲在女儿患病初期所言,每一个母亲都有护崽的天性,这种源自本能的冲动让她们可以无视年龄,随时做好为儿女奉献的准备——尽管,小孩曾因为无知背叛过家庭。
全片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当然来自母女间朝夕相伴的生活碎片,吴彦姝和奚美娟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在片中贡献了多个精彩瞬间。
考虑到很多人还没有看到成片,就不再对影片进行更多深度阐述,关于母女关系和各自的角色解读,相信每个人看完后都有自己的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较中秋档其他主打温情牌的电影,《春歌》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团圆之外的另一种结局。
尽管它面儿上说的是家庭内部的互助,但内里指向的却是这个民族最深层的集体记忆。
这份记忆曾经带来过强烈的刺痛,现在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代人的老去被逐渐遗忘。
母女间曾经的嫌隙均来自这份刺痛,现在却因为女儿的病得以修复。
这是悲剧,也是黑色幽默。
导演在片尾用一贯“正确”的方式提醒着观众,全国有更多类似的情况(阿兹海默症)亟待大家关注。
但坦率地说,比起身体上的病痛,精神层面的疾病似乎更值得深挖。
那段安全又无比正确的字幕虽然未尝不是来源于女性创作者的善意,但也有可能,相较背后的复杂,这只是另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
撰文 / Zed策划 / 轻年力量
6 ) 你爱的是春天
裴多菲·山陀尔《You like spring 》Petöfi Sándor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季秋季正和我相似,春天却像是你你红红的脸是春天的玫瑰我疲倦的眼光是秋天太阳的光辉假如我向前一步,再跨一步向前我将站到冬日寒冷的门边可是,我假如后退一步,你又跳一步向前,我们就一同住在美丽的热烈的夏天。
7 ) 有了温度,但少了精度
65岁的女儿独自照顾着85岁的母亲,然后,前者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一夜间,后者从被照顾者变成了照顾者。
女儿是很典型的那一代女儿,有主见有独立性,但长在新社会的教育里,过于朴素又过于收敛,远不及母亲那辈启蒙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能自带洒脱浪漫乃至任性的神采。
母亲是很典型的那一代母亲,有文化有修养有分寸,却也会在护犊时无视优雅、丢开教条,秒变超人和母狼。
它的设定其实非常好:强势与弱势、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在一场猝不及防的不可抗力间逆转倒置,自己已经是老人,自己的老人却还健在。
这是那批人正在背负的命运。
如果,衰退在作为子女的老人身上变成了一种加速度、有可能会对作为父母的老人实现弯道超车,该怎么办?
但它,有温度,却显得精度和完整度不足。
有时它看起来像李连杰和文章的《海洋天堂》,都在讲一个“在我的倒计时里,帮那个最在乎的人准备好没有我的日子”,区别只不过一个是爸爸对儿子,一个是女儿对妈妈。
有时它看起来像张艺谋的《归来》,同样是被摧残揉捏过的父亲,同样是选择过冷血然后懊悔终生的女儿,只不过,在那部片子里,丢失记忆的是母亲。
有时它看起来像反向版的《美丽人生》,当妈妈陪着女儿玩打仗游戏一样躲进床下,只不过一个是父亲在创造儿子的游戏幻觉、一个是母亲在迎合女儿的游戏幻觉。
它想要表达的几乎比它“看起来像”的还要多,它在这零零总总的表达里见筐就是菜,它一路忙于收纳与拼合,它找到了很多细腻入微的小确幸、小喜悦和小忧愁,但它并没有织成伟大的戏剧奇观,它催出了你许多眼泪,但它没有砸入你的心脏。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它对室内空间调度的使用相当极致,两个人在老宅屋宇和阳光的若干特定角度里移形换影,看着又像双人舞,又像敌进我退的博弈。
摄像机常常带着种“鬼视点”的味道,也许是看客已对父亲的逝去心知肚明、对二人的思念公约数心知肚明,这才起了“房中本该有第三方”的错觉。
它试着装进了太多东西:老龄化、女性、过去和现在、对抗与和解、知识分子、问题少年、甚至还有荒诞政治年代的人道灾难,再贯穿进一份日记遗稿的整理——一场抢救记忆的工程。
所以它会选择一对高知母女(她们的文化阶层和杨荔钠的上一部电影《春潮》截然相反),只有这种身份才能顺理成章地带出历史的创痕,以及,才有书写、言说的本能—代价就是许多观众会代入不了她们彼此间匠气爆表的语言和腔调,好像自始至终都活在舞台上。
它一直在讲的是家人和爱,可它在片尾字幕和短视频里,又斩钉截铁地把主题拉回到特别具象的地方,落定在阿尔茨海默氏症群体的关怀上。
它在亲情伦理中走了那么久,却在末端挂上了医学伦理。
它的标题是母亲,可它却一直在牵挂和愧疚于父亲。
因为它缺乏一种稳定的内在锚点,女儿的臆想,有时是安全感缺失,有时是童年复现,有时是渴望被认可,但她灵魂深处那个呼之欲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很明显“老年痴呆”只是一层外包装,导演用它包住的是心魔。
那心魔的内核为何物?
我们看到的,只仿佛精神分析学派收集的创伤案例汇总。
所以文淇的出现和反哺,会显得那么诡谲、突兀、忽至忽离、像个内心善念所编织的幻觉般不可信。
冯老师自始至终没表现出关于“孩子”的隐痛,“下一代”的缺失在她这里依旧归入对父亲的亏欠集群(等他回来我再出嫁),那她保护和救济文淇的心理动机来自哪里,何况这保护与救济的烈度,已经大到“替她顶下犯罪行为并被留案底”的程度,它绝不是一时的良心触发就能解释齐备。
更不说朱时茂的知心邻家大叔角色,有多么功能化、多么想当然了。
好在,细节依旧是动人的——这总归是世界上唯一的那个,当你尿湿了裤子时,会对你柔声说“不怕”、再把你搂入怀中的人——宿命在血缘至亲间,既是对赌协议,也是周而复始。
好在有两位老师化腐朽为神奇的演技。
好在有那么多,属于杭州的景观:西湖、西溪路、拱宸桥、茅家埠的通利古桥。
相比这些景观,结尾的大海,开始完全不加克制地把隐喻变成了明喻,就像《春潮》的最后的意象镜头里,春潮溢出缝隙、漫过城市每一寸的实地。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豆瓣&知乎ID:聆雨子
8 ) 立意发人深省
这并不是一部观赏性高的电影,台词脱离生活,过于书面话,还要加入一些俏皮的元素,就像夹生饭。
剧情和表演都不同程度的失真,家庭剧怎么排怎么导怎么演,建议多学学日本一些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山田洋次、松岗锭司、冲田修一等等。
但立意是发人深省的。
75 岁的女儿和 95 岁的母亲住在一起,就在女儿总是为好动的母亲发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女儿一生未婚,没有家庭和子女。
当这一对母女都进入老年之后,就暴露出了养老问题。
其实他们两个都算是老年人了,只不过一个是高龄老人,一个是老年人。
按照规律,都是那个相对年轻的来照顾那个相对不年轻的,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颠倒了这个赡养的顺序。
每个女人不一定是妈妈,但一定是女儿。
赡养似乎回退成了哺育。
当女儿内急跑到厕所,而发现已经小便失禁的时候,让我触动很大,其实人从婴幼儿发育长大,在某一个时刻,人又会回到婴幼儿的状态,大小便失禁、情绪失控、生活不能自理、器官虚弱。
据预测2035 我国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突破四亿,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叠加目前经济的情况,十年的时间,一个基础并不是很扎实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应对老龄化的机制吗
9 ) 观后
24.2.14.今天看了电影频道播的妈妈,大概前1/5开始看的,当然看的时候不知道是1/5,或者1/10?
但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演得真好,妈妈和女儿,都演得好好。
但最后因为恰晚饭还是啥原因,没看完。
文琪我也挺喜欢的,但我不知道她这个角色的意义,好像有点意义,但又好像没必要。
可能之后再去补完结尾吧,又或者重新看一次。
我不怎么了解阿兹海默症的病人的生活,但看片里我感觉挺现实的,而且真的能感觉到强烈的情感,坚强的爱意,母亲无私无畏的全心付出。
母爱真的很伟大,这种照顾病人的拉扯,可能只有母亲能坚持下去,那个下雨天的崩溃,也只有母亲还能坚持下去。
看着看着,也会恍惚间担心自己的以后,担心父母年纪也大了,自己能不能做好准备,有没有能力给父母好的照顾,能不能肩扛起来,自己又能不能赚到让自己能养老的钱。
我害怕,觉得自己太差,不能做到,害怕一切,怯懦不已。
阿兹海默和帕金森真的是费心费力的老年病。
真是想要一直做小孩子。
但看了片之后,也有在想要做怎样的老人。
还是,努力吧。
一点一点的,去做了它就不会什么都没有。
10 ) 《妈妈!》:母亲身份的再确认
“母亲”身份的再确认影片开头,展现了女儿冯济真对于母亲蒋玉芝的细致照顾以及生活起居的掌控欲。
在这里,母亲与女儿的身份俨然进行了调换,母亲成了女儿,女儿成了母亲。
随后,女儿冯济真患病,母亲蒋玉芝决定重拾“母亲”身份。
重拾的过程当中,穿插了众多女儿的童年家庭记忆,这也暗示着,女儿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再需要。
随着女儿病情的加重,母亲蒋玉芝在不适应和力不从心的状况下,再次接过家庭的重担,完成了她自身对于“母亲”身份再找回的确定。
可女儿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忘记了“母亲”的身份。
她像刚来到人世的孩童一样,重新认识母亲,并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再次完成了“母亲”身份的最终确认。
影片也就围绕着“母亲”身份的不断交换确认来展开叙事,其间洋溢着对母亲的无限赞美。
而“水”作为一个重要意象也参与了剧情的发展。
前两次皆以水面漫过冯济真的危险形式出现,预示了冯济真即将被病魔吞噬,失去自理能力。
第三次的“水”在梦中以湖泊的形式出现,湖底极其浑浊窒息,而作为知识阶级的冯济真把文字都抛洒在了湖面,暗示着父亲日记出版的喜悦下潜伏着危险。
第二天,冯济真就因为过于兴奋而摔伤了手,她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第四次的“水”已经完全漫过了冯济真,观众是以水底的视角看着冯济真,她已经深陷病魇当中,变成了一个老顽童,同时也失去了对于“母亲”身份的认识。
最后一次“水”是以大海的形式出现,母亲双手牵引着冯济真在海水中走路,并逐渐放手,让女儿扑进了她的怀里,随着女儿叫出了“妈妈”两个字,母亲的身份也再次完成了最终的确认。
关于“母亲”身份的探讨从总体上来看,整个故事不失恬静美好。
而这部电影几乎是杨荔钠导演近二十年以来最柔和的一部电影。
这可以从导演经常使用的意象——“水”就可以窥见一隅。
在《春梦》中,“水”代表女人无边的性欲,她既快乐又痛苦地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在《春潮》中,“水”代表的是女儿经年累月,长久无声的绝望哭泣。
“水”在杨荔钠导演的影片中一直是作为一个消极的存在的,而《妈妈!
》中的“水”最终指向的是母亲身份的重新认同,是美好希望的存在。
整体的画面风格也从过去的阴冷冰凉转向了《妈妈!
》的温暖黄色。
但这种叙事上的柔和,也大大削弱了杨荔钠导演一贯的犀利敏锐的执导风格,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不像杨荔钠导演的电影。
回看前作《春潮》,它表现的是女儿对母亲的极端控诉以及对母亲形象的不确定性。
正是因为《春潮》中母亲形象的毁灭崩塌,所以《妈妈!
》这部电影其实可以看作是,杨荔钠导演在她的电影宇宙里,对于“母亲”这一身份的完成。
但可惜的是,杨荔钠导演用了三部影片——《春梦》《春潮》《妈妈!
》,也没有完成对于“母亲”身份的确立,而新作《妈妈!
》更是流于中庸,丧失了一切犀利敏锐的观点。
它成了人们恋母的宣泄口,只能把它说成是一次成功的大众叙事。
再说回对于“母亲”身份的讨论,导演在《春梦》中对“母亲”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度的挖掘,但又因为叙述的重点大多都放在了母亲的性欲上面,对于“母亲”同是妻子、孙女的探讨则浅尝辄止。
《春潮》这部影片对母亲的虚伪自私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群母亲用母爱的无私来伪装自己过强的自我性,摧毁了孩童们心中的母亲形象,但这也不免有走向极端之嫌。
而说到《妈妈!
》,那它则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即作为母亲的过度自我牺牲。
把《春潮》和《妈妈!
》放在一起来看,前者批判了一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的自我性,后者则高度赞扬了一个母亲的自我奉献牺牲,这不仅两相矛盾,还有悖于社会的一个恒久命题——作为母亲在自我与奉献之间的取舍。
而杨荔钠导演对于母亲身份的探讨之所以走进死胡同,是因为这三部电影都过于情绪化,煽动性极强,以至于导演和观众都沉湎于情绪当中,丧失了大部分理性,引起了一定群众范围内的厌母或恋母上的情绪“暴动”。
《妈妈!
》中的人物符号——周夏《妈妈!
》中,周夏这个人物的存在饱受争议,很多人都认为导演在这个角色上花过多笔墨很没有必要。
但仔细分析下来,这个角色的存在有两个作用,其一是增加电影冲突,推动剧情发展,如公交车偷手机这段戏。
其二是导演借人物之口输出观点。
在电影中,周夏有说过这样一段话:“看似是你帮助了我,但也有可能是我成全了你。
”导演是在用“相互成就”这个概念来解释母女关系,她认为年迈的蒋玉芝为了照顾患病的女儿重拾“母亲”的身份,继续奉献自我,这虽然看似不公平,但或许蒋玉芝在帮助女儿的过程当中,也进一步完满了“母亲”这个身份,获得更深的自我满足感。
但我认为这种解释仍然是对成为母亲的女性的一种裹挟。
在前文中,有提到过《妈妈!
》这部电影非常偏离杨荔钠导演的一贯风格,但电影中一些细节的设置依稀也能看到导演过往的影子。
比如周夏这个人物三年后极具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再次回归。
这种现实与超现实的结合,在杨荔钠导演过往的影片中屡见不鲜,如《春梦》中的佛教蹦迪,鬼魂做爱,鬼娃转世。
《春潮》中的泪水决堤,流过大街小巷。
这些片段都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观感,并把主题的表达推向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但之所以周夏的回归如此突兀,是因为在《妈妈!
》中这种超现实与主题融合得并不巧妙,周夏这个人物几乎成了代替导演说话的工具人,所以引来很多争议。
《妈妈!
》的生活化叙事《妈妈!
》这部电影也采用了导演一贯的生活化叙事,这其中也有导演钟爱家庭题材的缘故。
但为什么《妈妈!
》相较于前作《春潮》是一次令人失望的探讨,且最终成为了一部合家欢电影,这从两部同题材同主题的电影的比较中可以窥见端倪。
一般采用生活化叙事的电影如果不注重戏剧性的话,会很容易流于平淡,而《春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表现上风轻云淡地叙事,但人物之间内部的矛盾却暗流涌动,《春潮》的戏剧性在主角郭建波沉默了大半部影片之后的内心独白中,达到了顶峰。
反观《妈妈!
》,对人物内心书写的缺失,使一切表达都浮于表面,而戏剧性也化作了外部的病魔,让人物显得更加单薄,那这样一个本就生活化的电影自然就流于平淡。
再加上人们对于知识分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整部电影也很容易被误解成一场知识分子的作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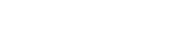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好看
摘取赫尔豪森职业生涯里最高光且最悲壮的生前一年时光,演绎他彪炳的人生。触觉敏锐、眼光超前、胆识过人、临危不惧,如果有幸不被日本赤军的衍生恐怖组织、德国红军派暗杀,他生命的延续,目测将会成为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的伟大政治家。赫尔豪森、CIA和红军派的三线叙事并最终闭环,清晰交代了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