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剧照
《诗》剧情介绍
许鞍华导演大学念文学时主修诗歌,感其解忧纾困,于是便一偿多年心愿,好好拍下香港的诗文风景。 电影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记录许鞍华导演亲自拜访多位香港诗人好友,如淮远、饮江、邓阿蓝、马若等会友论诗;并借用资料影像及照片,追怀已然离逝的西西和也斯。而整部电影的重点就落在第二部分已移居深圳,性格自由率性的诗人黄灿然及第三部分在台湾忙于讲学兼顾家庭,积极入世的诗人廖伟棠。香港诗或香港诗人宛如边缘的小草,在生活压迫挣扎的同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水班长许东奎出关朱弦玉磐普罗米亚前日谭七宗罪王妃总是要和离美式主妇第五季军曹大电影2:深海的公主是也五鼠闹东京兄弟同体勇者王FINAL外婆奔跑吧,少年放学后海堤日记温暖的皇妃画皮2性爱大师第四季死亡台球零秒出手:悬崖上的英雄盗非盗黑暗处留堂生大战僵尸绽放警犬赤龙女主播风云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光明的未来曼哈顿计划第二季直言真相第三季同事三分亲
《诗》长篇影评
1 ) 摘录——
原来许鞍华导演主修中文的时候,主攻的方向就是诗歌,她说想拍香港文学,尤其是香港新诗这个题材已经想了几十年了,但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像这样的片子不如剧情片那样有观众,找资金都非常困难,直到疫情前的那段时间,可能是把想拍的都拍过了,于是决定要完成这个愿望。
诗歌对她的意义是在她觉得很忧愁烦闷无助失败的时候,是在中小学时期念过的那些诗拯救了她,那些诗歌是她的护身符,这是她的切身体验,当然这并不是人人都会经历的。
淮远:我不赞成为了安全理由而自我晦涩化。
西西:我喜欢城市多点,买点云吞或莲藕粥、路过小食摊。
我不识写乡村、天堂或地狱,那就写我的城市吧。
饮江:我被自己写诗的行为和发生的状况带动写成最尾的作品。
也斯:寒意[含义]深入我们的骨骼,一个下午做许多徒劳的差使。
邓阿蓝:一走路就「跣」倒了,这个字是粤语来的,但经过生活的发展、磨练,这个词汇已经有形象、有美感。
黄灿然:「诗」这个东西真的有点神秘,你不能虚荣,一虚荣就没了。
所以我有一句话是:「努力不赚钱」。
因为经济离开香港,「经济流亡」反向从港迁回大陆,定居深圳洞背村。
现在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看我以前的诗,我没有不爱香港但也没有爱。
我永远在从这里离开,又永远在从别处归来。
在黎明的山岗,在曙光的航空站,我是夜以继日的抒情诗人。
由于除了西西都是男诗人,尤其黄灿然的《在茶餐厅》爹味美化之味太浓。
廖伟棠作为摄影师拍照竟然如此之好,短短几张城市的作品,就能激发我想写诗的冲动和纯粹。
香港人、定居台湾,他生我梦。
再说一万遍,廖伟棠作为鉴诗、赏诗者,在我心中真的排到很高的位置了,光是纪录片中刻意记录他讲课的浮光掠影——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都让我觉得辛波斯卡太会写,而他也太会理解,他是每位诗人重要的知己和翻译媒介,于是我说,成为大学老师是他的天赋的使命,他寻到了且做得很好,真想成为他的学生。
他说:不要去细究她爱的对象,关键在她爱的权利。
他从北京回到香港好像换了一个人,好像他的青春已经在北京用完了。
他原本是一个很内向、不屑于日常的人,但是在香港的十几年他变得更尊重日常生活。
从北京回到香港可能也是要和女朋友结婚,总之变得更实际了。
他是不相信沟通这件事情的,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喝酒和音乐人,他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范畴的朋友。
他的北漂时代对他我想是一段太特别的回忆,摄影作品那么多,文青年轻时。
即使在我眼中那样完美的生活,他也会羡慕着艺术家的朋友们,他没有那么想当一个好爸爸或者好老师,但为了生计和责任,他只能这样认真高强度的工作下去,以至于只要孩子睡着以后他都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每晚要喝酒,那才是他的解放时刻。
因为有了儿女的存在,我才过了很多平常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他们,我的人生完全就是看书和旅行旅行,当然不是游山玩水的那种。
和我养猫的感觉简直如出一辙。
他们那个年代的——推测是零几年,就连许鞍华导演也说:那个时候的北京可爱很多,现在就好像时尚杂志里面的一样,连相机都不想拿出来拍了。
当时在北京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被太阳烤焦了,烈日是很明显。
我写了首诗,讲北京的烈日,太猛,很毒辣,让每个人都很焦虑,我的朋友们尤其,每个都无由的焦虑起来,有创作的焦虑、政治的焦虑、爱情的焦虑——《灰心谣》,我少有的无比喜爱的他的诗。
还有《皇后码头歌谣》。
我认为写实摄影比其他艺术门类更有介入性,他不用想太多艺术的负担,当然还是会有的,办了一本杂志叫《看影像志》。
「我们尚好,除了还活着没有其他耻辱。
」「打倒象征主义,活生生的玫瑰万岁。
」——曼德尔施塔姆。
廖伟棠的片段会让我多加一颗星。
阿克梅派最高戒律:爱事物的存在更胜于事物本身,爱你自己的存在更胜于你自己。
类似于「存在先于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包含的能动性和变量胜于它本来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我们这些写诗的人就要去寻找和捕捉这个变量。
曼德尔斯塔姆的《词的本质》里面有说到上面那个句子,意思是:要在诗里呈现活生生的玫瑰,而不是玫瑰象征了美人、爱情、纯洁等等什么东西。
这个玫瑰是可感的,他自带隐喻,自带他自己的一切。
我们把它象征化、隐喻化的过程在削剪玫瑰的意义,是把玫瑰收窄了。
这和我们写诗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写诗的目的是要扩展事物的意义、扩展言词的意义。
正如策兰说的:「我是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
」对现实的界定,每个人有不同界定,对现实的深度每个人有不同的期待,当现实的深度到了一定时候,就会产生出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绝对隐喻」,他达到了一个绝对,这个绝对是指他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平衡是说他可以游离出它的意义,但他也可以回归它的意义。
所以策兰的诗甚至李商隐的诗,我们不去深究所谓的典故,不去挖它的隐喻的本体的时候,我们就看隐喻本身、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隐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出他的深度呢?
他同时是表面的,同时又是深刻的。
诗始终是在一个人最无助、最失败或最孤独时,才真正发挥作用。
同时,对诗的感受是很感性的。
布莱希特《致后代》也太绝了吧:这是一个什么时代?
当一次关于树的谈话也几乎是一次犯罪,因为它暗示着对许多恐怖保持沉默。
策兰的《一片叶子》是对这首诗的致敬和回应。
2 ) “诗”:一万种纪实的方式
本文2023.3.31首发于「凹凸镜」在《诗》片末,许鞍华被一群诗人问起,为什么要拍关于香港诗的纪录片?
她答,在许多压抑难熬的时候,是小时候读的那些诗成为了自己的护身符,给自己抚慰,支撑自己走下去。
她坦言对比剧情片,这种题材、包括纪录片的形式可能不足以吸引投资,不过想想自己最想拍的题材,还是放手来做了。
她做得很好。
有人拿《诗》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他们在岛屿写作》比较,许鞍华在映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不是因为看了《游》才拍《诗》,而是为了拍《诗》才去看以作参考。
”许鞍华鞍山出世,辗转至澳门,在香港长大,在港大比较文学系修读诗歌,后面去伦敦学电影,回来从胡金铨的助理做起慢慢拍电影。
我想起了《去日苦多》,香港回归之时许鞍华拍的一部纪录片。
在饭桌上,许鞍华和几位大学同学“吹水倾计”,和老友们拼凑旧时的记忆,北角的街道、五层楼高的模范村、街心公园的树荫,在《去日苦多》里我们看到宏大历史背景下殖民地的过往也是由个体微小的生活记忆构成。
时过境迁,等到了《诗》,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古稀之年的许鞍华,在纪录片中的呈现,对身份和城市境遇的挖掘,仍是那个“老文青”的身影。
她穿着深色棉麻长裙,桌边放一包莫吉托的香烟,和诗人对坐,在他们的工作室里、家里和茶餐厅里侃大山。
这样的对话,不过分解读,不刻意用力。
影片开头西西拿着泰迪熊对镜念《旧启德机场》,诗人饮江的《阴谋不沾染世界》贯穿始终,以布莱希特《致后代》结尾,诗人与城市松散自然地串在一起。
城市游走,“鹰都被我写过了”当第一个主要人物黄灿然出现时,许鞍华“套话”问他如何看待香港现状。
然后地点转向深圳,黄灿然牵着狗,在深圳洞背村的车站目送伴侣上车。
回到香港,在湾仔的天桥上,黄灿然说,朋友们都问他,你一个写城市的诗人,离开香港了你还写什么?
他望向天空回答,鹰都已经被我写过了。
一语道破所有最深沉的情感。
比起那些引发全场轰鸣的笑点和哭点,这是片中特别微不足道的一句话。
在香港生活的人或许会特别有共鸣,除了那些香港地让人熟悉的意象:茶餐厅、菠萝包、云吞面,比起摩登城市川流不息的街道人群,政治上汹涌不停的情愫,鹰可能是这个城市比较独特的存在。
生活在城市里的诗人,会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呢?
是写过的鹰,阳光,风、雨、云,和不忍打扰的裁缝店老人。
在此,我想引用片中出现的两首诗:阳光是伟大的 黄灿然“阳光是伟大的,因为他普照万物,而不知道并非万物都需要普照或同等普照,所以白云是伟大的,提供一层遮盖,还有乌云,增加浓度,所以雨是伟大的,使热的凉,干的湿,火的水,所以风是伟大的,使闷的畅,静的动,塞的通,所以劳动者是伟大的,给富人穷人所有人盖房子遮挡风吹雨打日晒,自己住棚屋,冷了就出来接受阳光的温暖,热了就移到他们建造的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 裁缝店 黄灿然我凌晨回家时,常常经过一家裁缝店——当它灯火通明时我才发觉我经过它,而它并不是夜夜都灯火通明。
我经过时总会看见一个身材清瘦、两鬓斑白的老人独自在熨衣服。
他干净整洁,一边熨衣服一边开着收音机,在同样整洁的店里。
每次看见这一掠而过的画面,我就会失落,尽管我的步伐节奏并没有放缓。
那一瞬间我希望我是他,这样安安静静地工作,像天堂一样没有干扰,让黑夜无限延长。
我不断闪过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的念头,但我的灵魂说:“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
” 这两首诗出现时,是我第一个泪目的时刻。
拍电影的,做纪录片的,影像工作者们有他们留住城市瞬间的方法。
许鞍华善于捕捉从小人物的生产图景,不管是《桃姐》还是《天水围的日与夜》,剧情片用故事起承转合营造社会底层的生活处境。
纪录片里,诗人的文字加上许鞍华对其文字所搭配的电影画面双重直击,效果翻倍。
对香港的怀念,对小人物的关怀,对街道质感的捕捉,逝去光影,旧时记忆与现实景象交织。
就像片中另一位诗人说,“跣”这个字是有画面的,这是香港这所城市内化成为港人生活体验后外露的表达痕迹。
“关键不在于爱的对象,而在于爱的权力。
”纪录片中的诗、人、城联动,直抵内心。
《诗》中引用黄灿然《阳光是伟大的》,《裁缝店》,《在茶餐厅里》配合捕捉香港地的普通人、草根劳动者、食客、路人的片刻,和文字回响,打破了好多好多堵墙。
喜欢纪实影像的朋友们或许在每一次真实影像出现时,心里都会涌出一阵本能的悸动。
我在此之前鲜少读诗,常常只沉溺在真实影像的一次元中寻找感动,而诗,给我开启了另一个次元的大门,不局限于表达的形式,因为种种表达其实都是在再现真实,超越真实。
感谢这部片子,一点也不“文”,也完全不闷,即使是少有文学经验的人如我,也数次泪目,完全感受到诗中、片中想营造的他者和自我纠缠的状态。
他令我尊重日常生活许鞍华说,她从来不知道廖伟棠是曾拍过她的摄影师。
这是廖伟棠的多重身份之一。
廖伟棠说,他认为沟通是无效的。
他上课从来不和学生沟通,三个小时的课讲完直接可以变成一本书。
既然如此,我们在片中看到的廖伟棠,就是那个单向输出的廖伟棠。
拍黄灿然时,许鞍华跟他一起生活,行山,煮饭、饮茶,补裤子。
拍廖伟棠,许鞍华则默默在一旁等待。
拍摄期间,这个自律又入世的人极度繁忙,那么许鞍华就拍他三个小时的课堂,在一旁听他的诗歌评审,记录他无数次的读诗、讲诗,直到所有的输出结束。
我们也和廖伟棠的学生一样,共同听了一节漫长的讲座。
他跟学生们从李商隐讲到策兰,讲入世的作家如杜甫、布莱希特;他批评别人的诗歌出现太多大词,如“民主自由”。
讲课的时间久了,一个长镜头太单调,我们就看到摄制组的第二个机位在画面边缘试探,正好就是廖老师在讲策兰的《一片叶子》:“当一次谈话/几乎就是犯罪”。
之后的穿帮,更为赤裸,摄影师大摇大摆地从画面中穿过,无数次地提醒我们拍摄的本质。
“打倒象征主义!
活生生的玫瑰万岁!
”作为纪实爱好者,我惊喜地发现有一些“彩蛋”出现在他那台有些年头,已经满是磕碰伤痕的MacBook air上。
这个摄影师的黑白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二十来岁的杜海滨、贾樟柯、赵已然、梁龙,出现在铁路沿线,在绿皮火车接口处抽烟,慢门记录曾经那些“游民们”年青的岁月。
廖伟棠也创建过纪实摄影的俱乐部,企图振兴70年代后就日渐式微的艺术形式。
他拍奥运前夕工人的状态,在鸟巢前记录即将被拆除的古庙。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西藏,去欧洲,给自己布置奇怪的任务。
廖伟棠把青春留在了北京和路上,回过头来,他结婚生子,在台北除了教书外,参与无数份社会上的工作。
廖伟棠说,是黄灿然教会他要尊重日常生活,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年幼的儿子派电动玩具火车偷偷潜入许鞍华和爸爸对话的现场,这是廖伟棠口中“超现实”的一幕。
2019年之后,疫情森严期间,在台北拍摄,也有其他港人作家出现在片中,可以联想到他们经受的双重压力。
片末借来影行者2007年拍过的宝贵素材,“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
廖伟棠出现在皇后码头保卫运动上,身份不断流转。
他在现场读诗,他是摄影师,更多时候他是在场的一员。
于是,这些林林总总加在一起,构建了他的诗人身份。
纪录片中还提到一首诗,我渴望找到出处,于是问chatgpt,它倒好,直接给我编了一首,也有意境。
剧透结束,还想透点“诗”,最末附上一些片中提到的诗歌。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在大荧幕上欣赏到这部影片。
阴谋不沾染世界 饮江 作为阴谋家活在没有阴谋这世界 其苦可想其乐可想 作为阴谋家阴谋不沾染世界其乐可想其苦可想 亲爱的你就是那个可想 阳光是伟大的 黄灿然 阳光是伟大的,因为他普照万物,而不知道并非万物都需要普照或同等普照,所以白云是伟大的,提供一层遮盖,还有乌云,增加浓度,所以雨是伟大的,使热的凉,干的湿,火的水,所以风是伟大的,使闷的畅,静的动,塞的通,所以劳动者是伟大的,给富人穷人所有人盖房子遮挡风吹雨打日晒,自己住棚屋,冷了就出来接受阳光的温暖,热了就移到他们建造的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裁缝店 黄灿然 我凌晨回家时,常常经过一家裁缝店——当它灯火通明时我才发觉我经过它,而它并不是夜夜都灯火通明。
我经过时总会看见一个身材清瘦、两鬓斑白的老人独自在熨衣服。
他干净整洁,一边熨衣服一边开着收音机,在同样整洁的店里。
每次看见这一掠而过的画面,我就会失落,尽管我的步伐节奏并没有放缓。
那一瞬间我希望我是他,这样安安静静地工作,像天堂一样没有干扰,让黑夜无限延长。
我不断闪过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的念头,但我的灵魂说:“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
” 在茶餐厅里 黄灿然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坐在斜对面的卡位里,他对面坐着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
他如此孱弱,近于卑贱,仅仅是这个形象,就足以构成他老婆离婚的理由——他多半是个离婚的男人,身上满是倒霉的痕迹,他没有任何声音,也不作任何暗示,却非常准确地照顾孩子吃饭;两个孩子都吃得规规矩矩,他们也没有任何声音,也不留意任何暗示。
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却不给他们明显的关注。
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男人,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定了,不会碰上另一个女人,也不会变成另一个男人,更不会有剩余的精力去讨好人,或憎恶人。
但是,在履行这个责任时,他身上隐藏着某种意义,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为他斜对面另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地感动着……….而他经历过的,正等待你去重复。
大角咀,寻春田花花幼稚园不遇 廖伟棠 这是另一个香港。
走在唐楼间漏下的阳光中看纸扎店里唱红梅记。
那些透明的身体里有心那些烧鹅有灵魂窗有扑翼声。
老孩子带领小孩子骑楼倦眠如一骑雨人在半途遇劫烂漫。
那些花哪儿去了?
他拿着一块砖头敲击彩虹。
还认得我吗?
我是你幻听的校长。
在猫眼里在狗爪里在潜过茫茫沧海的一条白饭鱼的怀里。
步步花花,亩亩春田,一江好梦全无恙。
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
皇后码头歌谣 廖伟棠 皇后码头歌谣共你凄风苦雨共你披星戴月——周耀辉《皇后大盗》那夜我看见一垂钓者把一根白烛放进码头前深水,给鬼魂们引路。
呜嗚,我是一阵风,在此萦绕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弈棋者把棋盘填字,似是九龙墨迹家谱零碎然而字字天书。
呜嗚,我是一阵风,在此萦绕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舞者把一袭白裙舞成流云,云上有金猴怒目切齿。
吁吁,我是一阵雨,在此淅沥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丧妻者鼓盆而歌,歌声清越仿如四十年前一少年无忌。
吁吁,我是一阵雨,在此淅沥不肯去。
“共你披星戴月......”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我共你煮雨焚风,唤一场熔炉中的飞霜。
咄咄,我是一个人,在此咬指、书空。
一片叶子 策兰一片叶子,无树的,献给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算是什么时代当一次谈话几乎就是犯罪因为它包含如此多说过的?
3 ) 诗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观影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消息我忍受了群里的叽叽歪歪我本可以不这样手忙脚乱但得给甲方查找一个“专家证”如今的每一分钱都不敢怠慢黄灿然足够的瘦削瘦削的人才配称为诗人瘦削的人穿什么都时髦他自称“经济流亡”从香港来了没听过的深圳洞背自从被海关收了书我就再没去过香港廖伟棠从北京去了香港又去了台北他是个“完整”的中国人他说诗的力量是在孤独中显现我也很想去台湾看看据说那里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据说那里能找回生活本来的节奏看了许鞍华的《诗》我决定写一首诗尽管我还拿不准这算不算诗
4 ) 一切关于诗
诗的意味在这里得到最大展现,譬如沿着读诗的声音一点点将画面补到文字上,但“老板搬一箱汽水”一句却呈现为水果店前的男人正挑拣一箱芒果,这样的场景,让原来的那首诗变成一个包含汽水的不可复制时刻,也让拍摄了“存在的是芒果而非汽水”的这一时刻的影像变成诗。
承认诗意味着承认一种语言的自然表达,接受有一点点虚荣心在里面的押韵(其实你甚至完全可以忘掉那点不成罪过的虚荣心),接受恋物与对风景的膜拜,接受某种矫揉与斤斤计较,因为它同时也是可爱而天真的。
接受它们的意义在于,当诗歌完成的一刻,或当诗歌完成后被诵读的某刻,人们会发现微妙之处生活有了受宽容与容纳的缝隙,在这里,生活不再只是被概括,而成了被描述。
我一直都不喜欢诗,因为我是废话很多、又不喜欢说话的人。
诗对语言的琢磨程度,让它像奢侈品一样空洞而难以把握、难以体认。
但因为它是语言的精华、文学的尖峰,像奢侈品总会变得奢侈一样,我也难免敬畏诗人。
我喜欢的小说家尤其给这种错觉开了坏头,他只有到临死时才放弃写诗而开始赚钱,而他赚钱的工具就是小说。
平日我难以察觉诗的精巧,像喝海水一样读诗集,把自己活活渴死。
惟有此时,以电影、以字幕、以语音,用足够察觉得到的时间流逝,以展现单单一首诗,这一文学形式才终于在我意识中浮现出来。
哦,原来诗是这样的,诗人是这样毫不露怯也不傲慢地写诗的。
我喜欢不来西西留恋的云吞面与莲藕粥,很大程度可能是我并未吃过真正好吃的香港菜。
她爱的香港也并非我舍不得的。
我通常愿意感受却不敢走近香港人对香港浓烈绵密的情结里,但我看到的香港只怕也如挑拣芒果的男人一样是某一刻仅存在于我身体里的香港,我以不同的语言、乱糟糟的心理、很难说得上是轻松的看待方式,完完全全改变了站在我对面两个闲聊者明天就会忘记的散漫谈天的面貌,他们不会知道,可是我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西西的香港,却很清楚我的香港。
我喜欢那些从Ann手肘旁摄入的画面、在导演与诗人间风吹水皱般的来回摇镜、仅展现半张脸的侧颜与仅右眼流下的泪,像Ann不经意间提到的,“因为我也要出现在里面……”而带来的日常。
惟有这样的日常是严肃的,而正反打(甚至仅正打)的采访才是娱乐化的。
一节课结束,廖伟棠刚要休息,Ann像放课后担心老师逃跑而急着问问题的学生一样疾走过来坐到他旁边道“我正有很想问你的……”,可她问了什么呢?
也许被剪在这一景之前,也许之后,或者根本不存在于我们视野之间。
而正因这样大咧咧正坐到对面,想问就问毫不在意最终话语会落到何处,让它在满足自我最高需求的同时成为最精致的作品,毕竟人对自己总是最好的。
5 ) 《詩》里的詩
淮遠《天堂無霧——悼戴天》「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飲江《陰謀不沾染世界》作為陰謀家活在沒有陰謀這世界其苦可想其樂可想作為陰謀家陰謀不沾染世界其樂可想其苦可想親愛的你就是那個可想《阳光是伟大的》黄灿然「阳光是伟大的,因为他普照万物,而不知道并非万物都需要普照或同等普照,所以白云是伟大的,提供一层遮盖,还有乌云,增加浓度,所以雨是伟大的,使热的凉,干的湿,火的水,所以风是伟大的,使闷的畅,静的动,塞的通,所以劳动者是伟大的,给富人穷人所有人盖房子遮挡风吹雨打日晒,自己住棚屋,冷了就出来接受阳光的温暖,热了就移到他们建造的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裁缝店》 黄灿然我凌晨回家时,常常经过一家裁缝店——当它灯火通明时我才发觉我经过它,而它并不是夜夜都灯火通明。
我经过时总会看见一个身材清瘦、两鬓斑白的老人独自在熨衣服。
他干净整洁,一边熨衣服一边开着收音机,在同样整洁的店里。
每次看见这一掠而过的画面,我就会失落,尽管我的步伐节奏并没有放缓。
那一瞬间我希望我是他,这样安安静静地工作,像天堂一样没有干扰,让黑夜无限延长。
我不断闪过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的念头,但我的灵魂说:“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
”《茶餐厅里》黄灿然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坐在斜对面的卡位里,他对面坐着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
他如此孱弱,近于卑贱,仅仅是这个形象,就足以构成他老婆离婚的理由——他多半是个离婚的男人,身上满是倒霉的痕迹,他没有任何声音,也不作任何暗示,却非常准确地照顾孩子吃饭;两个孩子都吃得规规矩矩,他们也没有任何声音,也不留意任何暗示。
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却不给他们明显的关注。
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男人,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定了,不会碰上另一个女人,也不会变成另一个男人,更不会有剩余的精力去讨好人,或憎恶人。
但是,在履行这个责任时,他身上隐藏着某种意义,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为他斜对面另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地感动着……而他经历过的,正等待你去重复。
《患难》黄灿然我的城市,今早我在山上,像往常一样回望你,像往常一样你笼罩在尘雾里,但此刻我才看见了你真实的形象:你轮廓模糊,与灰色云团浑成一体,只有高楼窗口里稀疏的灯火勉强描出一幢幢笨重的影子,使你显得那么无助,近乎悲壮;我突然对你产生一种深情,一种爱,不是怜悯,不是理解,而是正面的撞击:当太阳撕裂云团,穿透尘雾,向你输送强光,我突然感到我一直和你,并将继续和你患难与共。
《俯身》黃燦然当我沿着滨海街后半段走了几步准备像往常那样绕个弯去上班我突然想:何不从前半段走,目光穿过两边自然地生长的广告牌和蔬果档越过大马路,眺望树林覆盖的小山其实更自然,也更富生命气息。
而我刚转身按照我的想法走了几步,目光穿过两边自然地生长的广告牌和蔬果档越过大马路,眺望树林覆盖的小山,那树林呵便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声音,又好像是它向我传达我刚才那个想法而现在看见我听话地转身朝它走去便满怀喜悦,一簇簇膨胀高高升起,几乎是立体地向我俯身,如此清晰和逼近我甚至有点不自在,感到它就要蹲下来,把我抱起廖偉棠《大角咀尋春田花花幼稚園不遇》「这是另一个香港。
走在唐楼间漏下的阳光中看纸扎店里唱红梅记。
那些透明的身体里有心那些烧鹅有灵魂窗有扑翼声。
老孩子带领小孩子骑楼倦眠如一骑雨人在半途遇劫烂漫。
那些花哪儿去了?
他拿着一块砖头敲击彩虹。
还认得我吗?
我是你幻听的校长。
在猫眼里在狗爪里在潜过茫茫沧海的一条白饭鱼的怀里。
步步花花,畝畝春田,一江好夢全無恙。
它不是另一個,而就是這一個香港了」《皇后码头歌谣》 廖伟棠 皇后码头歌谣共你凄风苦雨共你披星戴月——周耀辉《皇后大盗》那夜我看见一垂钓者把一根白烛放进码头前深水,给鬼魂们引路。
呜嗚,我是一阵风,在此萦绕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弈棋者把棋盘填字,似是九龙墨迹家谱零碎然而字字天书。
呜嗚,我是一阵风,在此萦绕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舞者把一袭白裙舞成流云,云上有金猴怒目切齿。
吁吁,我是一阵雨,在此淅沥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丧妻者鼓盆而歌,歌声清越仿如四十年前一少年无忌。
吁吁,我是一阵雨,在此淅沥不肯去。
“共你披星戴月......”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我共你煮雨焚风,唤一场熔炉中的飞霜。
咄咄,我是一个人,在此咬指、书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致鲁迅》廖偉棠先生:我来信和你分一个梦,一条你也行过的山径,你也举手指点过的夕阳,乱山在梦中,未能捋平。
捋平也是伶俜,数日来我刻骨然后铭心,骨雕成了塔,心挖出原本的沟壑上面漂着一艘载酒的漏船。
这是你也写过的塔和船,依稀你也和我分过一个梦,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vagina,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但此时只有明灭与呜咽像我常常唱的一首国际歌,载着冰与火,撕咬着又幻变出许多灵光的火与冰。
是庾信远眺的,落星城,烽火照江明。
但先死者不是萧纲掀开夜幕,秉烛照见野路黄尘深。
后死者也不是庾信,我们不必并肩看一百年后的树犹如此!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我仍记得一百年前栽过这棵小树。
这个国家会好吗?
这柄剑,几回落叶又抽枝。
先生,谢谢这一个梦谢谢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
辛波斯卡《種種可能》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
我偏愛狄更斯勝過杜斯妥也夫斯基。
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勝過我對人類的愛。
我偏愛在手邊擺放針線,以備不時之需。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
我偏愛例外。
我偏愛及早離去。
我偏愛和醫生聊些別的話題。
我偏愛線條細緻的老式插畫。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我偏愛,就愛情而言,可以天天慶祝的不特定紀念日。
我偏愛不向我做任何承諾的道德家。
我偏愛狡猾的仁慈勝過過度可信的那種。
我偏愛穿便服的地球。
我偏愛被征服的國家勝過征服者。
我偏愛有些保留。
我偏愛混亂的地獄勝過秩序井然的地獄。
我偏愛格林童話勝過報紙頭版。
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
我偏愛尾巴沒被截短的狗。
我偏愛淡色的眼睛,因為我是黑眼珠。
我偏愛書桌的抽屜。
我偏愛許多此處未提及的事物勝過許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
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面的零。
我偏愛昆蟲的時間勝過星星的時間。
我偏愛敲擊木頭。
我偏愛不去問還要多久或什麼時候。
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策兰《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无树的,献给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算是什么时代当一次谈话几乎就是犯罪因为它包含如此多说过的?
黃燦然《哀歌之七》站在黎明的码头,我是黑夜的孤独者。
站在白天的故乡,我把出发的影子拉得比归来还长。
站在晨光中我理解到傍晚之所以被黑夜吞没的缘由。
我永远在从这里离开,又永远在从别处归来。
在大海的耳畔我把山风的叹息连给波涛。
在商业的中心我把祖国的神秘花朵藏于耳中。
在巴士上、火车上,在缓慢而平稳的轮船上我把奇异的目光投给玻璃山水、扑克面孔和同样冷漠的城镇和城镇。
在黎明的山岗,在曙光的航空站,我是夜以继日的抒情诗人。
在高速公路把生殖器插向乡村和乡村的地方我让缩小的影子退回到母亲子宫的黑暗之畔。
在科技的俯视下,在影像的风暴摧残心灵的都市,我已无所谓我更小的心灵遭受更大的摧残:我已无所谓星空的布袋囗收得更窄更紧,同样不在乎知识的皮肤萎缩或者光鲜,生出棱角或者淡出鸟来。
在城市神经渗出血丝的交通网,我乘坐无爱无恨的巴士、电车和诡秘的地铁,像水泥一样安稳地生活,像枯叶一样散步。
在鸿福大楼和国华大厦的出入囗,我每天出出入入,有所思,有所梦,有所得,有所失-反正無所謂
6 ) 铠甲|挽歌
此片内地应是无缘公放了,大家靠支援吧懂的懂,说回对岸#hkiff 久违的电影节开幕现场,逾千人夜晚场共坐于香港文化中心内,首映全程伴以欢笑、掌声和泪水。
《诗》/《Eligies》是许鞍华为电影取的中/英文名,亦似疫乱后,大地腾起挽歌。
没有更好的办法解释,但映日这一天,香港确然是落了一整日雨的。
影片中每一次启幕读诵诗行,我几乎不能控制眼泪。
其原由除过音画配合及文学语辞的雕琢力,诵诗的人声实在令人内心撼然!
诗韵那一刻被最高升华,沉吟的低语回荡着全部意义。
这场雨直到散场后的凌晨依旧未停,维港之上,云团氤氲,在高的灯火远处,夜晚的海面沉静出汹涌。
Ann已经76岁了,由这部戏看去,她是对从影生涯留存不得不做的东西进行了优先筛选,挽曲哀伤,锋利而温柔 ,似是她一辈子的孤绝却步履不停,也如同她镜头下的这些诗人和文字,他们所表达的一切都指向其身后那个,共同存在却早已看她不见的无依之地…倏记得木心晚年的纪录影像里他自述的那句:你要我毁灭,我不!
所以你如何能不敬重这样勇敢高贵的灵魂,况她是女子骨体,精神却有英然伟岸的铠甲,若不是她,无人能将这些画面以电影的规格在此一时献给香港,亦献给世界。
愿Ann被继续护佑!
写下这些随感的深夜里,全世界正在悼念坂本龙一先生的离世。
房间播放着教授为许鞍华导演《第一炉香》创作的原声音乐,幽离而盘桓的纪渊…
7 ) 和你說說《詩》
和你說說《詩》 廖偉棠 詩是平凡身軀裡面奇蹟一般的靈魂。
相信看了許鞍華紀錄片《詩》的觀眾,都會同意我這一感想。
試想從紀錄片開頭笑談拔鼻毛與打蟑螂之兩難的淮遠、到感念老友一張明信片的阿藍和馬若、到穿梭在深圳城中村和香港公共屋村的黃燦然、到應付沒完沒了的講課的我,其實都是平凡不過的華人男子(就像黃燦然的茶餐廳裡那個男人一樣沒有希望)。
不是他們寫出了詩,而是詩奇蹟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成為詩人:詩的載體。
於是他們擁有了一般人未必擁有的平行世界,他們也是「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的淮遠、說起詩與志時眼神熠熠的阿藍和馬若、堅信有一個詩神存在的黃燦然、和策蘭與布萊希特一起不甘噤聲的我⋯⋯許鞍華說詩是她的護身符,想必是她也看到我們身上那詩的護身符,於是以一部電影群之、興之、怨之也。
這樣一群人、這樣一部電影出現在華人地區以最刻板印象目之為文化沙漠的香港,豈不是詩一般的奇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當電影慢慢展開,我們的言語便超出了對詩的解釋、超出了為詩一辯,倘佯在香港的山水、碼頭與窮巷之上,克制哀思,而歸結於嗟嘆和詠歌——這就是《詩》的英文名字Elegies的本義,a poem of serious reflection, 充滿嚴肅的省思自鑑。
飄升縈迴於塵寰間,神來之處,有時讓我想起侯孝賢《刺客聶隱娘》裡那些無端聚散的霧或者嵐。
也許在香港觀眾眼裡,和這個「哀歌」最接近的,是「耶利米哀歌」的哀歌。
後者哀嘆耶路撒冷聖城的淪陷、聖民的受難,就像詩的第一句就說:「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
」——在希伯來原文中,本書名取自詩中的第一個字「艾卡」(Eikha),意思就是「何竟」。
不過,《詩》電影真沒有這麽悲情,它的魅力更像香港詩人的生命力,是從幽默、細緻和隱忍而來。
淮遠自不待言,慣以冷諷四兩撥千斤;飲江自不待言,能從絮語沉澱玄思和長情;阿藍自不待言,低聲唱吟工人藍調;西西自不待言,童真深藏微言大義⋯⋯從他們而來,香港需要的哀歌,是在一粥一飯一絲一縷之間,回首一傷神的。
所以即使我再荷戟徬徨,也能堅定地說出「步步花花,畝畝春田,/一江好夢全無恙。
/它不是另一個,/而就是這一個香港了」。
何況還有黃燦然,1997年信奉里爾克、葉慈的神秘主義的我初來香港時,正是他教我尊重日常不離地,既來之則安之寫香港之詩。
二十五年後,他在持續日常儉樸生活的表面下,收藏著一個真正的神秘主義詩人,他對世俗的凝視中混雜著藐視,因為他堅信詩是最高之物,高蹈雲間又輕盈降落茶餐廳和春秧街;但詩如他堅持搗爛的一杯檸茶裡的檸檬,如他施放未遂的兩包糖,安然自在。
是許鞍華的注視,用它們把他拉回人間。
這只是許鞍華懂得詩之三昧其中一個例證。
在鏡頭轉到土相的我身上時,她也沒有忘記尋找我身上的火,這火未必因為鬥爭、離散而來,也可以視為是「庾信遠眺的,落星城,烽火照江明」的那些劫火、魯迅相信的「地火」⋯⋯恰如片中我講課講到策蘭的「絕對隱喻」,我說的一句:「絕對隱喻是最表面的,也是最深層的」,它就像那一年我們須臾不可以摘下的那個口罩,一方面它遮住了我們的嘴巴,另一方面它象徵了我們沈默的決意,當它鋪天蓋地,就成了倔犟抗議者的盾牌。
許鞍華拍詩,但她使用的依然是她最擅長的散文,詩引誘解讀索隱,散文卻是閒庭信步,勝在坦誠與漫興。
這兩者形成的張力又恰恰就是電影的魅力,紀錄片拍攝於我從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的尾段、黃燦然從知天命走向耳順之年的尾段,卻是許鞍華「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的開始,這樣三者交聚,她在臨近結尾輕輕引出黃潤宇在而立之年前夕的淚水,鑑照了我們詩人、我城的故我並沒有白白努力。
詩在言外,可以說,在電影《詩》以外沒被讀出的99%的香港詩,更是《詩》的弦外之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你看,我又忍不住上詩歌課了,十年前我在香港電台開設過一個「和你說說詩」的節目,其實不只是為了普及現代詩,更是為了投石於香港人的池中,誘發更多詩的聲音。
而《詩》,又何嘗不是呢?
(原刊《上報》)
8 ) 献给香港的诗
许导终于拍了她最想拍的电影。
我一点也不意外。
回来的当天下午就去了电影院,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诗》。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除了以前去听过她的一次讲座。
我还在油麻地电影中心看 《I, Daniel Blake 》的时候遇到她了呢。
我们看的同一场。
她坐在后面。
我经常的时候看到她了,当时开心地朝她挥了挥手。
电影名为《诗》,英文的翻译是挽歌。
整个电影也像是许导送给香港这座城市的诗歌。
美极了。
如同电影里念的那些诗一样。
作为这座城市的移民,我也亲证了这座城的变化。
我目前这一辈子,算上我的家乡,一共在三座城市住过。
hk是成年以后我住过最久的地方。
头三年里,我永远只会去商场里那个挺贵的超市买东南。
卖的都是各种进口食品。
到了第四年,我搬出学校(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学校居住)。
直到那时,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生活(独立自主地生活)。
离开学校后住的第一个地方在一个街市附近,那是一个wet market(有海鲜档的是wet market)。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香港的菜也是分四季的,不是超市那样,一年四季卖的都是一样的外国进口的食物。
原来香港也有补衣服、收裤边的改衣档。
原来街市附近的家居用品店别有洞天、卖的商品玲琅满目。
原来街市卖的菜比超市里标明的产地要更细致:有云南的红姜、贵州的蔬菜、河南的山药、xx的大蒜、xx的皮蛋(我真的不记得了)、等等。
湖北蛋😊😊😊 我会想起外婆,她以前会走路去农村收土鸡蛋,然后一个人挑回城里卖掉。
也是在街市,我知道了每年柑橘出产的季节,好多摊主都会每天忙着剥橘子皮,用刀划出来漂亮的十字,一个一个的皮穿起来,一串一串的挂在那边,白绿相间,格外好看。
也是在街市,我知道了原来土茯苓非常非常坚硬,要用类似铡刀一样的东南才能切出片。
同样在街市,我知道了,原来海鲜档的海鲜并没有那么贵。
手打鲮鱼肉这么好吃。
我知道了原来每天下去6点,各个档铺,不论是卖肉,卖菜,还是卖水果,都会开始出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10蚊三个!
10蚊三个!
” 让人兴奋的不是那收市时候最便宜的价格,而是那些高昂的叫卖声带来的生命力和烟火气。
这种烟火气和内地城市清晨各种早餐店冒出的白色的水气一样,让人觉得心安,特有安全感。
也是在街市,我遇到了大年三十早上乖乖帮父母看铺子的小孩。
面对所有路过的客人在那边当面夸他懂事听话,小男孩淡定从容。
我给了他一个新年红包,他会非常礼貌的说谢谢。
同样在街市,我遇到了2023年都还只收10块钱的改裤长的林姑娘(深圳10年前都不是这个价了),一头白发,气质十分优雅,从来不急不躁,永远面带微笑。
非常优雅的林姑娘
存票根,又糊了。
不知为何,油麻地电影中心突然成了打卡地。
开关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油麻地电影中心和旁边的油麻地警署成了打卡地。
每次去都会遇到好多游客。
既然来了,不如进去看个电影吧。
下面是类似喵eye的app,可以看到所有电影在本地所有戏院的场次,还可以在线购票。
9 ) 许鞍华、黄灿然:关于《诗》
关于英文片名Elegies许鞍华:“片尾出现鸣谢的时候,有个画外音,是我在读诗。
由于这个时候不适合注明诗的来源,所以很多观众不知道这是谁的诗。
这是黄灿然的《哀歌》之七的片段,在影片里黄灿然的部分已经读过一次了。
为什么电影英文名叫做Elegies而不是Elegy呢?
那是因为黄灿然的《哀歌》一共有七首,英文名就应该叫做Elegies。
”(在《诗》第二场放映前的发言,2023.4.2)关于这部记录片黄灿然:“得知许鞍华要拍香港诗的记录片,我的感觉是很奇妙。
以她的年龄和名气,可谓德高望重,而她拍的题材,是所有香港事物中最没人知道的。
就像在黑暗的广场上,一盏聚光灯聚焦于一棵小树下的几株青草。
”(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上的发言,2023.3.30)黄灿然:“这部记录片虽然拍的是几个香港诗人,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关于香港诗的电影。
尤其是从我近年的接触来看,现在香港有一批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青年诗人,他们的前途是非常好的。
趁这个场合,我希望这些诗人能够有更多机会,包括在报纸杂志发表诗、谈文学,在机构和大学有更多关于诗方面的空间和可能性。
”(在《诗》首映前的发言,2023.3.30)
10 ) 诗的存在让人的绝望和力量成为永恒
借诗言政而不能。
许鞍华在这部纪录片里把“新诗”当成一个观察两岸三地人们精神出路(深圳、香港、台北)的工具,并试图寻找一个切片来观察。
在这场对话中,有人穷困拮据,自嘲从香港移居深圳为“经济流亡”;有人以忠于艺术的责任感抚养子女和兼顾教职,享受罗兰·巴特日记记录的巴黎旅行路线;有人想象服刑中的友人在狱中读到保罗·策兰的诗时会潸然泪下并为之伤感。
知识分子们在香港这个冷暖气候剧变的都市里浸泡过十几年,他们在奔向远方后一次次被将军澳、皇后码头和滨海街的集体记忆刺痛,在无须沉默的年代说了一次又一次,在该沉默的年代一字不发。
很明显我们面临信任崩塌的局面,两岸三地的华人暴露出强烈的疏离感,许鞍华用诗歌捕捉精神能量并试图提取出养分的努力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华人想到诗都会有隐隐作痛或精神颤抖的角落,因为“存在”这个命题是诗歌永恒的基调。
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并继续存在着,沉默的价值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显现,这是诗赋予困境中的人的想象、鼓舞或者无尽的安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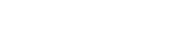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懂得怎么安慰别人…诗人就是这样的存在吧
看完这个后果然对黄灿然好讨厌
诗, 藏着诗人对人生的态度、对时代的观察、对情感的表达,在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时的抗争,每个认真写诗的人都值得被尊敬。(最近在看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的《西西看电影》,看到西西出场很是惊喜)
hkiff 文化中心:确实比贾樟柯高出不少。在讨论香港现代诗的流变中体现出导演极强的文学功底。全片饱含着对作为诗歌土壤的广东话和香港文化的深深眷恋。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拍摄更延伸出了和不同的地域背景所产生的有机互动,其中不少段落更是点出了当下香港创作者们的隐忧,穿帮镜头也仿佛是在回应“尊重生活”和“沉默”的议题,更不要说弥漫全片的疫情封控背景。非常棒的文学纪录片,同时也是很有意味的时代影像。
吴念真说许鞍华是他认识的导演里读书最多的,这部纪录片是她晚年的任性之作,不在乎观众只为自己兴趣而拍。那两个男诗人及其诗作我都没什么兴趣,所以这片子最大的看点还是许鞍华本人,每次她大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开心。还有她对香港的爱与关切,说起香港现状,问对方香港年轻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出路,然后没有答案,一切尽在不言中。临近结尾那个女孩说起给狱中的朋友写信谈诗,也比主角们更动人。
#hkiff47 結尾的對話,問Ann為什麼選了香港文學,她順其自然解釋因為詩一直給她以撫慰,從小學開始。但她沒有解釋「香港」,因為她拍香港就是理所當然,好像不需要向任何人任何解釋。不斷有一些隱晦的片段被引出來。問黃燦然如何面對審查,拍在台港人給坐監友人寫信,抄了策蘭的詩;廖偉棠引用布萊希特那篇致後代。這是小島的壓抑日常。謝謝Ann拍撫慰她的詩和詩人來撫慰大家。(廖偉棠拍的照片裡出現趙已然的瞬間我淚目了,開頭有西西讀詩的片段也讓人鼻酸(最後:爹的為什麼男詩人這麼多,看不得中老年文藝男&年輕女孩這種畸形拍拖組合!)
今天在资料馆问到许鞍华了,她说这部片已经拍完啦!期待!20230226“经济流亡”。又见许鞍华,跑跑楼变成追星现场。黄昏老人旅行vlog观感。20240122
现场看到了还是很有活力的ann导,(一如这座我久违的以为会有所变化但还是很繁忙的城市)当她回到最熟悉的香港拍她最想拍的题材,一切就变得很顺,是近年来难得的人文作品。以及借廖伟棠之口,廖又借策兰之口的那翻话,必将被下一位诗人捡起,继续在沉默之间书写下去。
许鞍华对香港诗歌的个人情感,或许想以“诗”为拍摄对象,但难度很高,最后的部分才显露出电影拍摄文学时文学本体的主体感。选择几位诗人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一起读诗讲诗谈诗,镜头再现诗,港人对港的情怀融入诗歌的历史和现实,凝结到诗之于个人意义里。
诗与电影都会帮助我们记住已经过去、正在经历与即将到来的时代。感谢还在写诗的人们与拍这部电影的许鞍华。
+
3.5。
感謝許鞍華。還在關心詩歌,且是香港的詩歌。
居然没有采用任何一位女诗人作为主角
看着导演奔走的背影,能感受到她对这个题材的热忱。计划了几十年,在当下拍出来却更有意义。不过总有种文不配题之感(可能是片名太大了),只有两个(男)诗人作为主体,编排似乎也并不设计,嗯……(能在大陆影院里看到这部片,还是感到很不真实)
没想到我居然能100%理解廖伟棠
看得非常感動,是許鞍華獻給香港文人的一封情書。很多詩人一直為群體發聲、為社會奔波、為價值拼搏,而看到他們不同的人生際遇,還是會感嘆理想與現實的博弈。「經濟流亡」與「政治流亡」,樹與沒有樹的葉子,打倒象徵與玫瑰萬歲,是全片最觸動我的三個點。有很多令人落淚的片段,也有很多能夠共鳴的詩詞畫面。詩人寫出的詩是有力量的,許鞍華鏡頭下的詩人同樣有力量。
淡 没能对上电波
以香港为母题,拍的却都是离开的人。
没忍住在快接近结尾的时候睡着了…有一些动人的部分,可总体也没那么动人。不过,很喜欢导演拍它的动机:因为想拍,而且一直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