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剧情介绍
1965年,印尼政府被军政府推翻,那些反对军事独裁的人都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并遭遇了血腥屠杀,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0万“共产党人”丧命,其中就包括农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华人。本片的主角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的元老人物。Anwar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Anwar讲述了他的故事,其中就包含着他年轻时候对美国黑帮电影的喜爱,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叛徒有你的小镇大海道完美绝配龙潭巨兽国王班底有的人活着有的人死了沉默之夜寻找马拉的奇幻之旅来拍怪兽电影吧!星际传奇2阿佤兄弟千分之一我的丑爹圣所萧红冒险三人组持续的爱狄仁杰之通天神教谍变1939源氏物语:千年之谜访客冰裂痴情的接吻逆温性感女特工夏日大作战献王虫谷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全球奇特运动之旅
《杀戮演绎》长篇影评
1 ) 我们,就这么看着他,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一个杀死无数人的老流氓,老去。
当流氓当了家,效果也许还不如土匪他们为了贬低共产党的形象,他们决定拍一些杀戮的影片,并引以为豪。
不禁让人想起了若干年前,无数小学生在影院看过的一些电影。
政权毕竟建立在杀戮之上。
作者拍这部片子,给西方世界震撼到了。
同样也给了世界一记重拳。
这些屠杀背后的‘自豪之情’和对‘睡眠质量’的担心,必将永远萦绕在刽子手身边。
一部好的纪录片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引起观者的反思。
的确,一件让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往事。
由在多少地方,多少历史上存在过呢。
当胖子赫尔曼坦诚自己竞选的目的时,不需太多联想,就会感到一丝凉意。
看着这几个老流氓在敞篷车上高谈阔论的谈着‘杀死所有中国人’的言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中国人。
最残忍的惩罚就是在你死之前告诉你,你所信仰的都是错的,而根本不给你忏悔的机会。
最后安瓦尔·冈戈回到当初的行刑地,无助地坐在地上,看着那些屠杀的工具,问:为什么我当初要杀死他们。
没有人回答他。
他干呕的声音,正如被他处决的人死前发出的声音一样。
也许他怀疑自己了,也许他渴望一个忏悔的机会。
但,他永远得不到了。
在死寂的处绝地,只有他和梦中瞪着他的眼神。
回应他的是历史的沉默和内心的梦魇。
而我们,就这么看着他,或嗤之以鼻,或是根本没有什么回应。
喝一杯咖啡,吃一片薯片,就这么看着,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一个杀死无数人的老流氓,老去。
2 ) 历史就在那儿,不悲不喜
由当年的刽子手自编自导自演一场发生在50年前、涉及250W人生命的大屠杀,这该不会是哪个邪典导演整出来的好莱坞大片吧?!
NoNoNo,它真实的发生了,印度尼西亚这一神奇的国度为这部大片献上最鼎力的赞助——多位领导人慷慨露脸激昂发声、五原则青年团橘花花乌泱泱的人肉背景,就这样,当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贫富悬殊的经济与从上至下未开化的思想与文明世界间垒起四方厚重的城墙,一场现实世界的超现实荒诞剧在城内上演了。
本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选择以纪录片而非剧情片的形式展现,先来看看纪录片的定义: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
既然不能用演员扮演,那我就用当事人演绎吧狡猾的导演打了一记绝美的擦边球,当印尼举国陷入极端激进的反共产主义橙色风暴中,当踩踏百万共产主义者躯体的Free Man登上印尼权力的最高峰,当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眉飞色舞讲述杀戮过程时,奥本海默隐去了自己的情感,不加评论,只是静静任由摄像机记录下安瓦尔•冈戈和他的Gangsters将一场反人类屠杀拍成好莱坞大片的全过程。
大概导演已深谙历史的本质,它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逻辑,分歧面前谁也强迫不了谁接受彼此的观点,谁也没有能力让谁彻底闭嘴,暴力屠杀或握手言和,历史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沉静的可怕,但是最终真相总会如抓不住的细沙渗漏渗漏直到彻底直白的展现于世人,娓娓道出历史的洪流——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
《杀戮演绎》便是借安瓦尔的电影在已破陋不堪的谎言上撕开一个真相的小口。
片中片导演安瓦尔•冈戈曾是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刽子手之一,亲自手刃1000余人,与剧情片中杀人狂一贯穷凶极恶狰狞的外表不同,现实中的刽子手竟是位面目慈祥、富有爱心、天真烂漫、痴迷电影的老顽童,不过想来如果没有他的这些特质,约书亚•奥本海默也撕不开真相的小口,成就不了《杀戮演绎》。
奥本海默在印尼的北苏门答腊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奥本海默让安瓦尔以自己的方式拍摄讲述这场屠杀,安瓦尔则像是叙述了一个自己重复做了50年的迷梦。
多年来他一直被噩梦缠绕黑夜,其他Gangsters说:“你感觉被鬼魂侵扰是因为意志太薄弱。
”一旦负罪感从生,防线崩溃非疯既死,杀人者只能继续以“坚强”的意志抵制潜意识对暴行的忏悔,找到不让自己感到罪恶的方法。
有的人挑眉炫耀“我使个眼神,他们就死了”,有的人双目圆睁“只有胜利者才能定义战争罪行”,安瓦尔选择了将梦魇如实的拍摄出来,并且渴望得到他人对其所作所为肯定的评价,正如片中关于女妖割下安瓦尔头颅变态虐待的情节应该放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的讨论以及圣洁的瀑布下被安瓦尔勒死的受害者拿出金灿灿的奖牌挂在他的脖上动情说道“因为把我处死把我送上了天堂,我要千百次的感谢你”,将这幕荒诞剧推向极致高潮,不禁感叹安瓦尔们真真是愚昧到无药可救,紧握真相砂砾的谎言之手真真是攥的紧,历史的公正性距离这个国度大概还有一个世纪之远吧。
转机意外出现,安瓦尔饰演一名将被处死的共产主义者,在经历了摧毁尊严的殴打拷问之后,当熟悉的铁丝套上安瓦尔的脖颈,突然他颤抖不止,无力瘫软,仿佛那个做了50年的噩梦成为现实,他询问导演、询问他人、询问自己:“曾被我拷打的人,是否和我当时感受到的一样?
难道,我犯了罪?
”无须别人作答,再回50年前的行刑之地,安瓦尔曾在此绿衣白裤嬉笑着舞一曲ChaCha,如今却抑制不住的干呕,用尽纸醉金迷掩埋的真相终究还是破口而出,历史公正性在个体身上的洗礼完成了,不禁期待谎言密布的黑暗中能有更多的人完成这样的洗礼与反思。
历史仍在那里不悲不喜,在它面前人性太是复杂,人力太过渺小,好与坏、对与错、白与黑都是太绝对的辞藻,不过历史终究会曲折的走向真善美。
最后,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政府否认历史的态度,是流淌着的血液带来的思考。
感谢《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给予我一种更加平和但又充满坚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洪流会冲刷掉一切费尽心思的谎言,真相经历时间的冲洗会愈加闪闪发亮不容避视。
我们会继续为历史的大白于世而奔走努力,而安瓦尔们终会完成历史的洗礼。
3 ) 三重杀戮、四种演绎和反身观看
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4 ) 你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人 --《杀戮演绎》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欢迎关注法律电影公众号“大抵浮生如梦”
5 ) 流氓社会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
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
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
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
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
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
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
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
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
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
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
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
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6 ) 《杀戮演绎》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
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
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
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7 ) 通过演电影换位思考减轻自己罪恶感
【6.8】1、这电影的评分多半来自其意义,意义是有的,记录嘛,但是真不好看2、印尼流民杀贡惨當,这些流民徒手杀人,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罪恶感,特别是那个男主角,他最后回到犯罪现场,那个呕吐我觉得应该还是真实的,至少看起来很真实。
但是真正的刽子手呢,那些憎渍家,赠腐,这些组织的头目,依旧没啥罪恶感,因为正如那个报社老板说的,他不用出手,手下自有人出手杀了他想杀的人,他没啥负罪感,这种才是最大的BUG。
3、人类因为群居才在自然界存活下来,所以人类的基因里就有厌恶族群相残的基因或者倾向,所以杀人狂魔人杀多了,也会内心不适。
4、整个电影比较无聊,一度看不下去。
历史上的屠杀太多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憎渍家的野心而死去的人更是比这多多了,一个人徒手杀一辈子,也不如憎渍家快
8 ) 赫尔佐格与莫里斯谈《杀戮行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9 ) 恶人之恶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10 ) 暴力反转
“流氓、混混”在一个国家,它的象征可以是什么?
也许是颓废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惹人生厌的街头一景,或者是无人拯救爹不疼娘不爱的模样。
但是,如果这个词和“自由”、“拯救国家”联系到一起,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
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
《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
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
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
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
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
”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
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
《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
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
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
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
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
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
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
我赢了我说了算。
”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
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
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
”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
”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
“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
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
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
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
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
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
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
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
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
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
那么下一代怎么办?
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
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
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
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
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
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
”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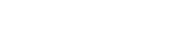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好看
摘取赫尔豪森职业生涯里最高光且最悲壮的生前一年时光,演绎他彪炳的人生。触觉敏锐、眼光超前、胆识过人、临危不惧,如果有幸不被日本赤军的衍生恐怖组织、德国红军派暗杀,他生命的延续,目测将会成为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的伟大政治家。赫尔豪森、CIA和红军派的三线叙事并最终闭环,清晰交代了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