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裘皮的维纳斯》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一间阴暗人稀的剧院之中,编剧托马斯(马修·阿马立克 Mathieu Amalric 饰)正在为他所改编的剧本《穿裘皮的维纳斯》寻找合适的女主角。接连面试的几位演员都令托马斯感到失望,她们和他脑海里完美的女神形象简直千差万别。面试以一无所获的结局结束了,正当托马斯准备离开之时,一位被淋成了落汤鸡的落魄女郎闯入了剧院。 女郎名叫旺达(艾玛纽尔·塞尼耶 Emmanuelle Seigner 饰),巧合的是,她与托马斯剧本中的女主角同名,可是,旺达粗鲁的举止和浅薄的学识让托马斯在内心里暗暗的否定了她。令托马斯感到惊讶的是,旺达不仅拥有全部的剧本,还自备了戏服,在旺达的一再坚持下,托马斯同意了她想要试演的请求,并且亲自与她对戏。就这样,在瓢泼大雨之中,一场关于男人与女人、命令与服从的好戏拉开了帷幕。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大变局之梦回甲午A货B货喜欢你是你猫与桃花源练手3之乱世巨星引以为戒2春潮山海蓝图无畏警官2名校风暴第四季遗骸刀尖上行走你是我兄弟之牌王名扬花鼓圣剑双面生活涉谷怪谈2雾都魅影影子舞者亲子鉴定师手记失落世界的统治者新白蛇传之青蛇紫禁秘录香巴拉疑犯追踪第四季截路拦杀反起跑线联盟2猎狼者天使面庞爱在梦醒时分
《穿裘皮的维纳斯》长篇影评
1 ) 男人和女人之间,情欲最难掌控。
男女间的调情,自古以来就是一场较量。
挑眉弄眼,顾盼神飞。
被情欲支使的人类有本领让自己突然熠熠生辉,也有邪念让对方俯首称耳。
没错。
归根结底,情欲也是权欲,你爱一个人,想征服他,想控制他,想占有他。
这不是少见多怪的作死,而是深埋于心的本能。
当这种欲望被渲染到极致,我们在性爱中,就出现了SM关系(虐恋)。
S施虐者,通过控制M获得快感。
M受虐者,通过受控于S获得享受。
而二者必须同时满足为对方及自己的欲望服务的意旨,才能获得一种被上帝眷顾的感觉。
又由于有情感作用其中,它也绝对不是单纯的主奴关系。
今天我们讲的这部电影,就把SM关系诠释得非常清楚和酣畅。
电影名字叫——
《穿裘皮的维纳斯》故事发生在一间阴暗人稀的剧院。
夜深人静,冬雨落落。
男主托马斯在灯火通明的剧院里打电话抱怨。
他正在为自己的新剧《穿裘皮的维纳斯》没有找到女主角而焦心。
《穿裘皮的维纳斯》是19世纪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著名虐恋小说,这出戏讲的就是个SM的故事。
这时,一个女人淋着雨,推开了门,摇曳生姿。
她是来试戏的。
女人飞快地讲述了自己从巴黎的另一端赶来试戏的不容易。
她脱下大衣,呈现出一个带着项圈、穿着皮革紧身衣大胸女人。
我从来不乐于把性感与胸大划上等号,但这样的场景却不免充满了性暗示。
女人解释说自己这样穿来是为了帮助自己「进入角色」。
她说自己叫旺达,恰好跟这部戏的女主角名字一样。
在这部电影里,演员的一切语言和行为都要进行双重解读。
因为整个影片基本都是托马斯和旺达两个人在对戏。
戏假情真。
导演通过对戏的过程一步步揭露自己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并且建立起两人的SM关系——支配与被支配。
所以旺达说「进入角色」,除了进入剧本中的角色外,还要进入SM关系中的角色。
托马斯拒绝着说「不」,在这里看起来,都饶有意味。
他在防御。
但是他拒绝不了她。
她换上衣服,调整好灯光和仪容,甚至对着舞台上的仙人掌做出性爱的姿势,她入戏了。
旺达说出台词的那一瞬间,你几乎无法想象托马斯的讶异。
仿佛她突然换了一个人,端庄优雅,又饱含着樱桃般神秘的诱惑。
在她的感染下,他也缓缓地走到了戏里。
托马斯念起对白:「对裘皮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那是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激情。
抚摸着柔软浓密的裘皮,有种特别的瘙痒感,犹如电流……」
他这番话,再次赤裸裸地把本片的性暗示解释了出来。
影片名字和这部戏的名字都叫《穿裘皮的维纳斯》,所谓维纳斯,是女神;所谓裘皮,这里则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女性的阴部。
旺达优异的表现缓和了两人的关系。
托马斯继续读着台词,「你觉得咖啡好喝吗?
」旺达答,「我只喝了一点,不过它棒极了。
」
紧接着旺达跳出角色来问托马斯,「所以这个咖啡就是象征之类的吗,咖啡就是他。
她只尝了他一点,就兴奋起来了。
」「你这可是把我看透了。
」托马斯耸肩。
他是角色,又是编剧和导演。
在这部戏所设定的19世纪,「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我爱你」,这句子便算是色情了。
托马斯继续假借角色之口讲述自己那个穿着裘皮的姨母。
那是他小时候的事。
「她来到我的房间......脱下裘皮,卷起长袖…… 我试着逃跑,另外两个女人抓住我,脱下了我的裤子,把我扔在裘皮上,我一点不敢动,而姨母就用她的权杖惩罚我。
我裸露的屁股和大腿就像着火一样……直到我哀求她停止,求她饶了我。
」说着,托马斯的瞳孔放大,仿佛回到了那个晚上——他亲吻着虐待他的姨母的脚,向她道谢,注视她离开。
他说,那一瞬间,他被造就了。
旺达同情地看着他,「噢,真可怜。
」
托马斯笑着摇头,「不,她教会了我全世界最珍贵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什么比疼痛更性感,能比堕落更刺激。
」他的这番自白一如《纸牌屋》中Frank曾说过的,这世界上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只关乎权力。
因为托马斯儿时曾经受到姨母的「统治」,他竟爱上了那种感觉。
爱上疼痛——只因为疼痛无比性感。
而随着慢慢地对戏,旺达与剧本中的女主角合而为一了。
她的对白,慢慢蒙上了一层超乎时代的女权主义色彩。
「在我们的社会,女人只能通过男人获得权力,我想知道,当女人和男人平等,他们之间会变成什么样。
当她们成为她们自己。
」
在SM关系中,女性是可以占据主动作为施虐方而存在的——这恰好正是一种女性对男权的有力反抗。
然而更有力的胜利,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精神控制。
于是她再次借问他,「怎么,已经爱上我了吗?
」
他既作为角色,又作为自己,「至死不渝。
」而旺达并不好对付。
托马斯在他扮演的角色里据理力争,愿做旺达的奴隶,直到永远。
旺达问他是否把这称之为爱情,他说「这是唯一的爱情。
」这既是台词,也是托马斯内心的真实世界。
在他看来,爱情如同政治,只有一方才能掌权。
一个必须愿打,一个必须愿挨。
他们对彼此,或者不如直接说是托马斯对旺达的情欲,被撩拨得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不由问旺达,「你到底是谁?
」他越问就陷得越深。
因为他发现自己哪怕不知道答案,也愿意被她驯服——不用问,她是他的维纳斯。
至此,旺达在二人的关系里开始真正掌握了主动权。
他们开始排练一场壁炉边的戏。
她设计了新的剧情,除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衣服,性感风骚地要求导演把他裹在「裘皮」里。
似排练,非排练;似引诱,未引诱。
这就是许多导演喜欢通过「戏中戏」来塑造角色的原因,它让角色之间的关系暧昧而明确。
随后旺达「进攻」起来。
她开始猜测托马斯真实的私人生活,包括他的女友。
她几乎全部说对了。
托马斯想说些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没有发现的是,此时躺在沙发上的他,一如刚刚躺在沙发上的旺达。
而旺达戴上了眼镜,穿上了他的西装。
这个神秘女人的真实身份在此刻呼之欲出。
她是一个托马斯臆想出来的人物——旺达是托马斯幻想中的维纳斯。
表面上他与「正常人」无异,而真实的他,是那样渴望疯狂和堕落。
他渴望一段真正自由的S与M的感情。
所以当旺达说自己演不了,要走的时候,他跪在了她面前——他跪在了自己的臆想对象面前——也跪在了自己的欲望面前。
「她」就是他的欲望。
「她」的主宰权在一步步扩大。
她一步步地要求他,放弃他的尊严,以及他脑中的桎梏。
「她」也带给他,那种,美妙的疼痛。
他,疯狂地在自己的戏剧世界里起舞。
而此时,旺达也开始一再嘲笑托马斯的戏剧俗套和幼稚。
托马斯很不开心。
他从旺达的包里拿出了她的靴子替她穿上。
「她」成为他的女主人,肆意凌辱他,他进一步性奋起来。
旺达穿着她权力的靴子走过来,摘下自己脖子上的项圈,套到了托马斯脖子上。
他彻底成为她的奴仆。
这一切,马斯都在内心深处想象过无数次。
而旺达说出了更深层的真相——托马斯在这个故事里,更需要被满足。
他自始至终都在寻找那种被「统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事实上存在于所有的爱情里。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仔细想,所有的爱情都有角色扮演的成分,区别只是程度轻重罢了。
这电影就是在说这个。
「你应该自己演旺达的。
」旺达说。
她走过去,给托马斯披上了所谓的裘皮。
而他深深地享受着。
她给他涂上鲜艳的口红,穿上华丽的高跟鞋,给予他一个性感的女人所需要的性感。
他已经被驯服了。
他像一条狗一样被她拖到舞台中央象征着阳具的仙人掌道具边上,捆绑起来,不能动弹。
阳具,在这里,象征着比欲望更具体的——男性之欲。
旺达用尽力气扇打无法动弹的托马斯。
一如托马斯的隐欲折磨他。
她是托马斯的旺达,亦是上帝的旺达。
一如故事最初,剧本扉页上写着的、那句来自《圣经》的箴言:「上主惩罚他,便把他叫到一个女人手中。
」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男权社会形势下,上帝对于男女关系制衡的计策。
最后,旺达离开,而托马斯被绑在自己的“阳具”上继续煎熬。
这是导演对男性最后的一抹轻蔑的嘲笑。
艺术家便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叛逆。
戏中戏,情中情,欲中欲。
在波兰斯基的眼中,我们所有人都相似地把用红布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我们本来,都一样的疯狂。
「爱,与被爱,这该多么幸福。
但更美更有力量的是,这吞噬了我的折磨。
」致维纳斯,
致我纷纷的情欲。
—THE END —公众号:宋问题电影里的女人。
来玩~
2 ) 典型的法式小众电影
很多时候在法国或欧洲被看好的电影在中国却很难被欣赏。
这部电影正是这种类型。
一部电影却更像是一出话剧。
两个演员在一个封闭空间从头说到尾。
如果不是喜欢文学或为了练习法语,则很难看下去。
对话中蕴涵着很多人生哲理社会逻辑。
应该说在欧洲它也应该是个小众电影。
看这个电影要有耐心,然而,光有耐心可能还很难看下去,我只看了一半便放弃了。
3 ) 《穿裘皮的维纳斯》:一只名叫德里达的狗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4769.html一扇门关上,镜头离开了舞台,只有被绑着的托马在挣扎;另一扇门关上,镜头从剧院里出来,“面试请进”却已走向了结束;最后一扇门关上,只留下雷电中寂静的剧院,外面空无一人。
关上,关上,再关上,世界以如此隔绝的方式被封闭起来,而一切却在里面真实发生着——托马不是剧中的塞弗林,戏剧也不是排演的《穿裘皮的维纳斯》。
关上,关上,再关上,是对于一开始门被打开、打开、再打开的回应,开门和关门就构筑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从空无一人的街道,到“面试请进”的剧院,再到面试已经结束的舞台,在依次打开的过程中,雷电一直还在,外面的雷电和里面的雷电,在同时响起的雷声和闪现的光线中构建了一种同时性的结构,也正是这种在关闭中被打开的世界变成了独立的舞台,它允许人进入,允许人演出,允许人改编,最后当然也允许人颠覆。
进入和改编,演出和颠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而在这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托马和旺达一方面进入到文本里成为演员,另一方面却在创造着文本,成为文本里的演员是一种被动的接纳,甚至是取消现实中自我的属性,而创造文本,却以主动的方式完成命名。
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一个关于权力转换的过程,权力是剧本里伯爵姨妈手上的权杖,是舞台中央象征男性器官的柱子,也是作为改编者托马对于旺达演戏的要求,但是,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如托马所说:“这是唯一的爱情,就像政治。
”爱情中爱与被爱构成了权力的结构,政治中的控制和被控制构成了权力的体系,但是它们是不稳定的,它们做好了改变的准备,也正是有着这种可能性,使得权力充满了诱惑,也会为权力付出代价。
文本的权力化,然后是“反权力化”,这便是这个打开的世界里可能性的意义。
在这里,文本是多重的,第一个文本是1870年由马索克创作的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这部小说是SM的经典作品,因为第一次定义了“受虐癖”,所以称为一部“性爱圣经”,而作者马索克(Masoch)的名字因为与“受虐癖”(Masochism)发音相似,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同源性关系;而第二个文本则是托马根据马索克的小说改编的剧本,《穿裘皮的维纳斯》虽然是话剧的名字,但是这种同名性却并非是重复,当淋湿了的旺达最后来到面试现场,她对话剧的评价是:“这是一部SM的色情剧。
”这是一种大众意义上的评价,旺达还只是在马索克的文本里,但是托马却驳斥了她的观点,“这是美妙的爱情故事,这是伟大的小说。
”从托马坚持自我的肯定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改写这部小说,赋予其自我的理解,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剧本就挣脱了马索克的文本,提供了走向主动的可能;而第三个文本则是在剧院里排演的这出话剧,其实,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排演,因为一天下来“面试”已经结束,托马已经要离开舞台,而旺达在大雨中淋湿了衣服,迟到的她甚至在托马的拒绝中准备走出去,但是最后却没有取消,当两个人在交流、在对话、在试探中,却完成了非标准的面试,甚至排练的过程不断添加、修改剧本,最后变成了另一部话剧。
从马索克的小说,到托马改编的剧本,再到托马和旺达共同完成的话剧,电影构建了三重文本,三重文本不是同源性的,它们创造了可能,它们建构了秩序,它们改写了结局,就像权力一样,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结构,它总是在改编,在转化,甚至在颠覆。
在这个封闭的剧院里,这种对于权力关系的改写是如何发生的?
它是渐进的,缓慢的,甚至是自然的,一开始,托马接完了未婚妻的电话,就告诉她今天来面试的人没有一个满意的,那些演员看起来像妓女,这是一种否定的开始,而当门打开进来的是全身淋湿的女人,托马也以否定的方式回绝了她:“我们要找的人跟你不一样。
”本来如果按照这样发展,托马结束了一天的面试回到未婚妻那里共进晚餐,而失去了一次机会的旺达则沮丧地再次走进雷电交加的街上,整个文本也便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终结。
但是这一切没有这样发生,即使旺达似乎对剧本一点不懂,即使托马第一眼看到认为完全不符合自己对人物的设定,即使两个人对于马索克的书是色情读物还是爱情故事发生了争执,但是文本却以另外的方式开始了改写,而终其原因,就是权力以潜伏的方式找到了一个出口,托马是这部话剧的剧本作者,他一再申明只是改编者,但是从他一天下来对于女演员的面试可以看出,他需要有人让他有一种权力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演员的调度和控制,按照自己设想在舞台上演绎。
所以当旺达出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即使她不是自己满意的人选,但是正是因为不满意才有可能使她拥有更多的权力。
而在另一方面,旺达似乎以她的神秘性吸引了托马,她的名字是旺达,而这个名字和剧中的女主角名字一样,所以她对托马说:“我注定要演这个角色。
”而且,不在面试名单上的旺达却拥有完整的剧本,她的那只黑色包里还有买来的戏服——不仅有女主角的戏服,还有40欧元买来的男主角的衣服,还有剧中出现的那双靴子,甚至她脖子上那个黑色项圈,刚好符合SM的道具要求,只是裘皮似乎没有,那条围巾替代了裘皮,却也具有某种诱惑,而且她还懂得舞台的打光。
实际上,神秘的旺达出现在托马面前,像是有备而来,而她在迟到之后推门而入,就是让这个空间变得更为封闭,也正是在这种设定中,旺达反而拥有了另一种权力,那就是引诱者的权力:脱掉外套,她就展露出自己性感的身材;她对托马斯的那种眼光有着明显的勾引成分,而她说到项圈时说:“这是我站街的时候戴上去的。
”她马上说是开玩笑的,但对于托马来说,似乎正打开另一个世界;而登上舞台的时候,她说那根柱子是“阴茎的象征”,并走到那里做出交合的动作……身体、眼神、语言、动作,似乎都让她在托马面前变成了引诱者,而引诱的意义就是通过一种权力来控制别人。
一方面是托马作为改编者对于剧本和演员的控制欲望,另一方面是旺达以引诱者的身份实行了反控制,所以权力向着两个维度发展,男人和女人,导演和演员,主动和被动,便以微妙的关系在此起彼伏中阐释着关于权力的翻转。
第一阶段是进入,当旺达假装穿上裘皮,当她完成绕口令联系,当她将咀嚼的口香糖黏在灯控台的桌沿,当她改变了舞台上的光线,于是“面试”开始了。
本来托马只是单纯的面试官,但是在没有男主角的情况下,他客串了演员,当他穿上旺达为他准备的那件1869年的服装,于是他也进入到了这个即兴创作的文本里。
在这个意义上,旺达和托马是平等的,正是有平等地“进入”,才会在权力结构中产生新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开始进入的第一阶段,托马作为主动者,他控制着这个文本的走向,他是权力的中心。
“生活在某个不可预知的瞬间造就了我们。
”托马念着台词,他和旺达进入到自己的剧本里。
而在这个剧本里,权力就表现为一种控制力,而这种控制力表现在施虐和受虐组成的对应关系里,但是施虐和受虐也是不稳定的。
那个名叫塞弗林的男人由于小时候被穿裘皮的伯爵姨母用桦树枝鞭打,于是产生了一种受虐的倾向,一开始塞弗林是抗拒的,当枝条鞭打下来的时候,他试着逃跑,但是伯爵姨妈却抓住了他,最后打得“他的屁股和大腿就像着了火”,还让他亲自己的脚。
而这便成为了“不可预知的瞬间”,“从此,裘皮不仅仅是裘皮,那一瞬间,它造就了我。
”姨母每天都来,每天都打他,塞弗林开始享受这个受虐的过程,并且立下愿望,要娶一个穿着裘皮的女人为妻,而这个娶女人的愿望并非是一种男人的权力欲望,而是像姨母那样,在裘皮创造的瞬间体验被虐的过程。
“没有什么比堕落更刺激。
”“我必须追求肉欲的快乐。
”所以当他在温泉旅馆里遇见穿裘皮的女人旺达之后,希望她就是那个维纳斯,“驯服我吧,支配我吧,打我也行。
”他把她叫做“女主人”,把自己称作是“奴隶”,并且把这种情感称作是“爱情”:“我对爱情全身心的投入。
”而在这个封闭的剧院里,一切似乎像话剧一样演绎着,但是,剧中塞弗林是一个受虐者,是处在被支配的地位,而旺达是施虐者,是支配他的女人,但是在剧外,托马是改编者,是面试官,他是支配者,也就是在剧中和剧外两个空间里,权力的关系是反向的,而正是这种反向的关系,使得演绎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可能。
在第一阶段进入之后,托马的确把握着主动,他驳斥旺达把这部戏叫做“虐童戏”,他告诉她阿芙洛狄忒就是维纳斯,他指挥她站在舞台那个象征权力的位置上……但是当他们被托马未婚妻的电话打断之后,便进入了第二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反转开始发生了。
他们先是拿掉了本来在手上的剧本,像是真正进入到创作阶段;本来他们喝咖啡完全是手势的动作,而在这时,托马拿起了茶杯,旺达后来也倒了一杯水;那件替代裘皮的围巾在剧中托马为她披上,而转身之后,旺达又把它拿掉了——披上是剧中,拿掉则是剧外,这个简单动作就是打破了文本之间的界限,故事在剧本里发生,也在舞台上发生,剧本已经写好,而舞台上的演绎却正在进行。
托马说:“在我看来,在塞弗林看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先是说到了“我”,接着马上改口是“塞弗林”,他让自己回到了剧本中,而逃离剧本似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欲望;旺达说:“我是维纳斯,你在勾引我吗?
”她是在回答托马的那个问题:“你是谁啊》旺达小姐?
”“旺达”既是剧本中的旺达,也是作为演员的旺达,在这个“你是谁”的问题又变成了一种歧义,而“你在勾引我”更像是一种现实里的问题。
一切都开始了变化,在这个阶段,托马一直强调的是剧本是“开放式”的,他还对看过原著的旺达说,表演可以临时发挥,而当旺达建议让塞弗林说话时带一点德语口音,托马受到了启发,于是他说:“我们有权创造角色。
”于是在“创作”中,托马饰演的塞弗林开始写日记,旺达开始模拟夜莺和猫的叫声……在这个阶段,他们加入了即兴元素,实际上他们开始了对于剧本的改写,在改写过程中,托马已经慢慢丧失了控制权,而旺达明显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权力,虽然不是很明显,看上去是配合托马,但是这一种转换已经开始靠近剧本中塞弗林被支配的结局。
又是未婚妻的电话打破了两个人的表演,于是在搁掉电话继续中,他们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旺达明显占据了主动,她先是从托马未婚妻的电话开始引出话题:“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瞬间了?
”剧本里塞弗林被某个不可预知的瞬间改变,但是现实里呢?
托马在接电话时的唯唯诺诺就表示他实际上是处在被支配的地位,所以旺达看穿了这一点,从而用这样一句话让托马引起共鸣,后来旺达又猜测说托马的未婚妻是女权主义者,她拥有一头秀发,拥有明眸,拥有细长的双腿和性感的身材,还有一条拉布拉多的狗,“它叫什么名字?
”“叫德里达。
”托马在回答的时候,其实已经朝着旺达设定的方向前进,她的每一个猜测似乎都是正确的,后来旺达说:“我是私家侦探,你未婚妻让我来监视你。
”这样完全让托马出于被动的位置。
而在对剧本的意见里,旺达也开始表现出主动性,当托马说:“在你内心深处乐于支配一个男人。
”旺达马上就说:“不,不,我受不了这台词,有性别歧视。
”当托马否认这是歧视的时候,旺达甚至质问他为什么改编剧本,“这甚至已经不是剧本了。
”托马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了探索内心的激情,塞弗林唤醒了她的欲望。
”一开始是争执,托马甚至骂她什么也不懂,并且说:“不管你演不演,再见。
”但是当旺达更坚决地要离开的时候,托马却又道歉:“对,你说的对,我接受所有你说的。
”看起来他决定了旺达的去留,掌握着剧本的主动权,但是当他开始挽留旺达,其实主动权只是象征性的,它已经变成了退让,甚至哀求,于是当未婚妻的电话再次响起,旺达完全占据了主动,“从此以后你听我的,从此以后你叫托马。
”第一句是台词,旺达成为了塞弗林眼中“穿裘皮的维纳斯”,成了控制自己的“女主人”,而第二句已经变成了现实,这种命名就是让托马完全进入到了旺达设计的文本里。
她让托马打电话给未婚妻,说“再见”,然后扔掉了手机;她让托马从包里拿出性感的皮靴,让他为自己穿上;他把自己的项圈拿下来,戴在了托马的脖子上;她以对剧本不熟悉为由,让托马来演旺达,给他穿上裘皮,画上口红,穿上自己的鞋子,然后用丝袜把他绑在那根柱子上,“这全是一场戏?
都是假的。
”旺达这样说,然后打托马巴掌,真的就这样打在了脸上,然后旺达说的那句话是:“你以为可以随便利用一个女演员,满足你变态的幻想?
”彻底的反转,彻底的颠覆,彻底的改写,当托马被绑在“阴茎的象征”的巨大柱子上的时候,男性的权力在这一刻完全消失了,连同消失的还有作为改编者、作为面试官的权力,而旺达从一个没有机会的迟到者,到被面试的演员,再到剧中的维纳斯,到“女主人”,最终成为施虐者、支配者,从而拥有了权力。
这是对于剧本的颠覆,却以戏剧化的方式创造了新的文本——最后,在灯光灭掉再次亮起来的时候,从舞台上消失的旺达再次出现,“让我们起舞吧!
”在酒神之舞中,她真的披上了裘皮,裘皮里真的是赤身裸体,而这只是对于诱惑的反讽:被绑在柱子上的托马没有了主动性,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权力,而这个文本最后的注解就是那一句话:“上主惩罚他,把他交到一个女人的手中。
”男人和女人,诱惑和被诱惑,支配和被支配,以及施虐和受虐,在文本的不断改写中,在舞台的即兴演出中,权力关系从来不是稳固的,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在改变和颠覆,总是会形成新的结构,而这个新的结构便是创造,便是命名,托马把马索克的小说叫做“爱情故事”,旺达让自己拥有和剧中人物一样的名字,托马把诱惑者称作是“穿裘皮的维纳斯”,旺达在表演时离开了剧本把他叫“托马”,这都变成了一种改写式的命名,命名改变了结构,颠覆了关系,所以无处不在的权力只不过是一种命名的象征,就像那条拉布拉多狗,用德里达这个著名哲学家的名字命名,它是解构,也是建构,它是文本,也是现实,它在台上,也在台下,它的门最后被关上,也早已经被打开。
4 ) 多元视角的间离
电影中的电影,如教科书一般。
极简的元素,一个场景两个演员,一个半小时就讲了一个复制、多元的故事,呈现一次情欲的困兽斗。
影片的主线,即是一个驯服的过程,精彩在于女主如何一步一步的驯服和撕破男主,把男主的脆弱和欲望曝光。
导演玩了好几次的多重关系和多义性。
1、电影故事是讲一个话剧导演改编的一部sm小说,跳出电影来说,波兰斯基同样是在改变这部小说,只是以戏中戏的方式来演绎和改编小说。
这个巧思太好玩了。
2、入戏和出戏的无缝切换,从一开始明显的区分,到后来电影角色与小说人物融为一体。
电影有两条平行的故事线,明线是话剧角色的驯服,暗线是女主对导演的驯服、调教。
3、话剧中有一个维纳斯,是天降的女神,而电影角色的女主,也像一个维纳斯一般,就像开了一半的上帝视角,玩弄着男主,最终地位调转。
电影留了非常多线索,来证明女主不简单,也就留下多重解释,1、女主是男主幻想,2、女主真的是维纳斯 3、女主就是一个s,来调教男主的。
电影最精彩的就是入戏和出戏的无缝对接,形成的三视角,话剧角色、演员、观众。
比起姜文拙劣的间离效果,波兰斯基更加聪明与成熟,他在电影中创造一个假定的剧场,电影角色围绕着假定的剧场来出戏,依次做到间离效果,而不会对观众产生迷惑和不适。
当电影角色与话剧角色不断的无缝切换,观众以为是电影角色的对话时,醒悟过来已经切换到话剧角色时,间离效果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根本不需要再强调。
这是高明。
电影角色与话剧角色的对话重叠的部分,就像电影剪辑的j-cut和l-cut,j-cut用的最多,这就出现了,那一句台词是同时适用于现实与话剧之中,惊喜也就由此尝试,观众会得到一种兴奋感、满足感。
我会觉得这部电影是教科书式的,导演用的元素是极简的,可以说把电影的本质元素抽取出来,重剑无锋的感觉。
一个剧院,两个角色,却一点都不沉闷,反而波涛汹涌,其重点就是角色的关系和地位不断的流动与转变,一个封闭的空间,确是如此开放。
他们的关系一开始是男强女弱,随着男主越来越入戏,慢慢的戏中的女强男弱渐渐的映射进入现实,到了最终魔怔时,发生了一次小变奏,让男女主所演的话剧角色调转,反串。
接着迎来男主彻底成为俘虏,受到惩罚,男主演的是话剧中女主的角色,也就是说,sm的关系中,他们是相互的被虐待。
一次有意思的sm探讨,男主就是一个m,随着越来越入戏,一点一点的被卸去伪装,女主始终是清醒的,驯服着男主。
5 ) 权利之上的“义务”
女演员夺门而入,不惜采取弱者甚至是牺牲色相来博得编剧的好感,这时编辑是有权利的,但他的权利是因为有女演员想面试这个依托,所以这个权利才成立,但如果面对一个过街的老鼠,编剧除了喊打之外,他没有任何可以行使的权利。
同样,女演员最后有了权利,并把编剧玩弄于鼓掌之上,是因为她之前做出了牺牲,并利用了编剧渴求好演员的心里。
女演员是有才华的,但她的才华只有被编剧这个伯乐视中才能称其为才华,才能利用这个才华作威作福,如果她面对一个吃骨头的狗,她的才华可能比不上骨头更加性感。
权利和义务是一体两面,没有单独的权利也没有单独的义务,只是权利和义务不一定都来自于同一个个体。
权利之所以被称为权利,是因为有一个个体需要被权利填补或者他有义务为这个权利做一个注解、去承担这个权利所释放出的能量。
也就是说,权利的存在不可能缺少义务的润色,如果没有一个个体把“承受”这个义务扛在肩上,权利就成了无的放矢,就如同施虐者需要受虐者的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演出。
上主惩罚他,把他交到一个女性的手上——性别歧视;姨母鞭打——虐童;一份接受男主为奴隶的合同——有准备的骚货。
女演员用这些来表示出编剧的改编一点也不成功。
随后,女演员改编了一场戏开始给编剧导戏,利用编剧想让戏剧完美的心态、爱惜才华的心理勾引之,给他下套。
并在讲述了一套自己诠释的、原作是性别歧视、变态、色情小说之后的理论后,尽管编剧生气,但女演员赌赢了,她成功抓住编剧不愿放弃她这个优秀演员的情势,彻底掌握了主动。
女演员认为编剧的戏剧充满了对女性的蔑视,认为编剧的初衷就是错的,是带有原罪的,而利用弱点去攻击敌人,当弱点被克服就会止血,但利用欲望去克敌,则会挫骨扬灰。
欲望是一个人堕落的源头,而欲望总是代表着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毫无节制的上纲上线,尤其是爱欲,不是为了我爱你,只是为了我爱你所以你也要爱我,甚至不惜沦落为受虐者,让爱慕的人站在施虐者的高度,让他用极端而洒脱的行为表现出他对自己的爱怜,证明自我正在被人疼惜,仍然会受到别人重视。
通常会认为“求糟蹋”的人充满着无限的下贱,秀出了自身卑鄙的灵魂与失落的心房,而实施者是正义的化身,代表了上帝来惩罚人类,是善心来的。
一个人可以放低身段、接受肉体的折磨,甚至是感官的侮辱,降格为一个受虐者,只是为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心里变态与性冲动?
这里面就没有什么感动与爱慕?
欲望和慈悲的区别大概一个是为了自己,一个是为了他人,但施虐与受虐到底哪个是为了自己、哪个是为了他人又该如何区分?
人们可以说受虐者虽然遭到肉体削减但是他的精神是愉悦的,所以这个是欲望,施虐者虽然应用了暴力但是他的精神是痛苦的,他只是为了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所以这个是慈悲的。
据影片来看,演员与导演权利的变化,变来变去都是导演是受虐者,不管导演扮演的是男性还是女性。
施虐和受虐是没有性别依据的,不能因为DNA的不同就决定了角色。
施虐和受虐无疑都是摄影机后面的导演来决定的,他认为原作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强烈的情感碰撞”,压根不是什么“当代缺失的激情”,这本书、这出剧都是一堆圣屎(Holy shit),他完全是为了戏耍戏剧的导演造了一个女演员“旺达”来实现他的意图。
只是最后被绑在柱子上的还是一位“女性”,尽管这是男主脑补出来的一个女性,但是并不能因为被绑着的人带把就说是雄性,不知这算不算性别歧视(惩罚一个人都要把他先忽悠成异性。
)然而,男主作为一个编剧,为什么会白痴似的步入陷阱,合理化的解释就是:演员可以诠释任何一个角色,何况是编剧。
人性的千千万万足以去塑造万万千千的角色,只是平时碍于行为规范或者法律准绳人们才没有表现出戏剧中角色的疯狂,但一旦有一个可以大展手脚,又不用负责任何后果,甚至还有钱赚、还可以发展出被称之为演技的口碑,何乐而不为!
演员不是在出演角色,也不是本色演出,而是在出演自我、出演人性。
所以,有了人性的武装,一切的剧情都能说得通,也就是男主导演为何白痴到了一定程度。
总之,为了人物的个性与剧情的冲突,人物是可以经常“突变”的,而高手和新手的区别就是这个转变是生硬的、还是柔顺的。
6 ) 《穿裘皮的維納斯》中的快感呈現與批判
一、序言《穿裘皮的維納斯》(法語:La Vénus à la fourrure)是由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於2013年上映。
同名小說發表於1870年,是奧地利作家利奧波德·馬索克(Sacher-Masoch)的代表作,講述的了一位迷戀一個穿裘皮的寡婦的貴族甘心成為她的奴隸、受她驅使,最終被那女子拋棄而轉向宣稱男人應當支配女人的故事。
文中男主人公有著明顯的戀物情結(fetishism)和受虐癖(masochism)傾向,masochism一詞正是來源於作家馬索克的名字。
電影改編保留了小說的主要情節,仍以男子與穿裘皮的女子的虐戀故事為主體,但採取了“戲中戲”的形式:影片中男主角托馬斯在為他改編成戲劇的《穿裘皮的維納斯》尋找合適的女主角,并親自與前來試鏡的女演員旺達對戲。
兩個人在表演的過程中逐漸碰撞出火花,托馬斯的受虐癖傾向被穿裘皮的旺達激發,但電影結局卻與小說的主題相悖:小說重在描述此前為被人發現的受虐癖的心路歷程,將之引入人們的視線;而電影則引入了酒神女祭司的暗線,通過象征的手法在結尾對受虐癖背後的菲勒斯中心主義下的男性快感進行批判,更顯導演獨運匠心。
本文試圖通過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受虐癖為切入點,探尋這種特質是否有違男性快感,再從戀物情結出發,具體分析電影中的幾個片段,試圖解釋電影中的男性快感是如何獲得的,以及它們與受虐癖的聯繫。
最後,分析電影結尾的酒神女祭司的出現,反思前半部分電影中呈現出的男性快感是如何被電影自身審視的。
最後一部分兩種價值觀的衝突也是筆者選擇分析這篇電影的原因。
二、受虐癖引發對權力的顛覆電影中的男主角托馬斯作為戲劇導演,在面對前來試鏡的演員旺達時,自然是處於權力主導地位的,應該是他來決定旺達的台詞、表演和心理狀態。
與此同時,戲中人塞弗林則是想臣服於一位女子腳下,任由這位主人虐待驅使,滿足於這種相處模式中的愛情,此時劇中的寡婦旺達(與女演員同名)在這段關係中占主導。
電影中的權力關係不斷發生顛覆,是與受虐癖的特質有關係的。
在德勒茲(Deleuze)的論述中,受虐癖並不是承受施虐癖(Sadism)的對應者,兩者之間有很大區別。
施虐癖通常採用祈使句和說明性質的語言,避免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即非自然狀態的文明世界中產生的激情和愛意,強迫性地試圖將理想狀態變為現實,如冷漠的浪蕩子一般享受著極端但又充滿示範性的客觀理性的樂趣。
[1]受虐癖與施虐癖一樣心裡有著理想的形象,但並不試圖將其引入生活中,而是中止現實生活,通過如同幻想一般的超感覺(supra-sensual)將現實中的那個角色提升為理想,視施虐的愛人為女神。
此外,受虐癖偏好勸說性、對話性的語言,引誘并鼓勵被提升為理想的那個人向自己施虐。
[2]因此應當注意,下文提及的施虐者指的是受虐癖的女神,是與施虐癖截然不同的。
電影中第一次重要的權力顛覆發生在第61分鐘,導演托馬斯不滿演員旺達對戲劇主題的理解,旺達憤而罷演,導演連忙追上來說:“好吧,你是對的,我接受所有你說的,我們能繼續了嗎?
求你了,旺達。
”鏡頭仰拍站在觀眾席最後面換衣服的旺達,再切換到俯拍由低處的舞台向上走來宛如朝聖的托馬斯,最後一個過肩鏡頭中托馬斯手拿劇本激動地顫抖抬起,旺達居高臨下地正面走向鏡頭,從他手中接過了劇本。
此前托馬斯雖然在扮演塞弗林時向旺達卑躬屈膝,但所作所為都在導演自己的掌控與期待之中。
而到了這裡,作為導演的話語權發生了第一次動搖,戲劇的主題思想任由旺達改變,劇本交接的瞬間象征著托馬斯將作為導演時擁有的權力一並拱手相讓,極力勸說旺達剝奪他的主動權,可見現實中的他也因受虐癖的影響而向女神屈服。
然而受虐癖雖然將主導權轉交給了施虐的一方,但在這段關係中真正的掌權者實際上正是受虐癖。
電影借旺達之口道破了這一點:“你不在我的支配之下,是我被玩弄於你的股掌之中。
你是我的奴隸,卻在操縱我。
”隨即旺達出戲,以演員身份評價這段關係:“他一直說她有權力,可實際上他才有權力,她沒有。
他越服從,反而越支配。
”正如雷諾·伯格(Ronald Bogue)在分析德勒茲的文章時所言,受虐癖主角看似被掌握主導權的女子教訓、改造,但實際上是他在將她塑形,他使她穿著符合他的喜好、向她提示她該訓斥他的話,“受害者是在通過他的虐待者而非他自己來表達。
”[3]因為塞弗林對裘皮的偏好,旺達才總是穿著裘皮出現;因為塞弗林渴望被女神虐待,旺達才扮演起虐待他的女神。
德勒茲的分析對看似主僕的權力關係造成了顛覆,支配這段關係的是受虐癖對快感的追求,這種快感既包括賦權的快感也包括會在下文將詳細分析的觀看與戀物的快感,為此他才要不斷勸說施虐者繼續施虐,影片中權力關係的第二次顛覆此時業已完成。
三、觀看與戀物的快感電影中男女主角有過多次換裝,男主角始終衣冠楚楚、穿著保守,而女主角接近一半的時間只穿暴露的內衣進行表演,對於在鏡頭面前袒露身體毫不介意(當然是導演波蘭斯基的要求),比如在電影第63分鐘旺達從胸衣里取出合約,這個動作暴露了她的乳房,裸露的乳尖位於畫面的正中心,牢牢吸引了塞弗林的目光(如圖一,見附錄)。
乳尖暴露與否對於劇情並無影響,但電影最終選擇暴露則說明影片中的女性是無可否認的作為被觀賞的對象而呈現於男性凝視(male gaze)之下的——被電影中的男性注視、被攝像機注視,也被電影外的觀眾注視,這也是主流電影把色情編入父系秩序的敘事語言的表現。
[4]再比如影片76分鐘時,旺達半躺在維納斯坐過的躺椅上,雙腿大開,塞弗林距離很近地半跪在她的雙腿中間侍候她穿上及膝的皮靴。
塞弗林為她穿第一隻靴子的過程是由一個過肩鏡頭拍攝的,畫面中除卻塞弗林之外只能看見旺達的半個背影和一條腿(如圖二),隱去了對旺達性器官所在的部位的表現使這個場景看起來宛如普通的僕人侍候主人,並不令人覺得色情。
但在塞弗林給第二隻靴子拉上拉鏈時,鏡頭切換到塞弗林視角,只見他顫抖的手和長靴的特寫。
他的手緩慢地向上移動,宛如愛撫過旺達的腿,鏡頭隨著手的移動徐徐上移,直到畫面中出現旺達的大腿根部——雪白的皮膚與黑絲襪和黑皮靴形成鮮明對比(如圖三),戛然而止,再切回過肩鏡頭。
第一次拉上拉鏈用時4秒,第二次通過男性凝視(male gaze)來色情地看(looking)時則長達20秒。
弗洛伊德曾在《性慾三論》(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和《本能及其变迁》(Insti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中闡述過觀看癖(scopophilia)的概念,它是性本能的成分之一,“最初屬於前生殖器階段的自淫,而後,看的快感就通過類比轉移到他人身上”,是“使被看的對象從屬於有控制力的、好奇的凝視之下”從而獲得快感的色情基礎。
[5]即便旺達在這段關係中看似是作為主導者的(在不考慮第二重顛覆的前提下),依然是女性作為被觀看的對象而存在——不論是作為滿足電影男主角女神理想的觀賞對象,還是作為承擔影片色情意義的電影角色。
而所謂的色情意義,指的是從男性凝視的角度出發,使觀眾獲得性刺激而獲得視覺快感的符合父系秩序的意義。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這種父系秩序是菲勒斯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的表現。
菲勒斯(Phallus)不同於陰莖(penis),它作為一種象征符號,是一種關於缺乏的能指,並不指代一個具體的、確定的現實對象,所以菲勒斯代表女性的缺乏(lack),也代表了女性慾望的能指。
菲勒斯處於母嬰關係的核心位置,嬰兒在成長的過程中會發現母親沒有陰莖,他們認為是父親剝奪(priver)了母親的菲勒斯,從而產生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
[6]電影中女性的形象會引起男性焦慮——她沒有菲勒斯,這意味著男性面臨著閹割的威脅。
男性無意識中為了逃避這種焦慮,有時會採取徹底否定閹割的方法,即通過向物戀對象投注感情以代替向她,或把她轉化為物戀對象,將她物化成女神來崇拜。
[7]電影《穿裘皮的維納斯》就是採用這種方式來逃避閹割焦慮的:無論是托馬斯還是塞弗林,都對裘皮相當迷戀;而作為受虐癖,對應本文第二部分中德勒茲的論述,會將向自己施虐的愛人崇高化、視作理想中的女神。
“維納斯”不只是旺達的象征身份,更直接出現在了托馬斯拍攝的戲劇中、塞弗林的夢境里:影片第46分鐘時,遇見旺達之前的塞弗林虔誠而又興奮地為(旺達扮演的)裸體的維納斯披上了裘皮。
雖然塞弗林拒絕了夢境中維納斯的誘惑,但在第二天便立即臣服在了旺達腳下。
不禁令人想起弗洛伊德的那句話:“被壓抑者終將回歸。
”[8]通過戀物情結和女神崇拜,男主角擺脫了閹割焦慮。
結合戀物的觀看癖,又使電影即便不表現做愛過程,把中心放在如何滿足男性凝視之上,也能產生并傳達出情慾快感。
四、由維納斯到酒神的女祭司電影與原著小說最大的區別便是引入了酒神女祭司的意象,從而徹底推翻并改寫了原著的主題,造成影片最大的反轉,也對前87分鐘的菲勒斯中心主義下的男性快感進行了無情批判。
在結尾,托馬斯扮演起了被激發出受虐癖的劇中人旺達,心甘情願地被演員旺達綁在了代表菲勒斯的高大仙人掌塑像上,本期待著旺達會順“她”心意地羞辱、輕蔑、支配“她”,但旺達從角色扮演中跳脫出來,不屑地叱責道:“甘願在男人面前做如此手足無措的可憐娼妓,是對女人的侮辱,是淫穢色情!
”托馬斯一直以來勸說旺達的“充滿激情的愛”只是一場掩飾,掩飾了從頭到尾都是男性為滿足自己的快感而侮辱和支配女性的真相。
旺達揭穿了這一切,盛怒之下抽了托馬斯幾個耳光,並要求他感謝。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對托馬斯的凌虐已經不再是受虐癖期待的那種虐待。
受虐癖嚮往的虐待來自理想中的女神,而不是一個局外人,畢竟受虐是從屬於性的,終極目的還是滿足自己的快感。
電影結尾的旺達已經不再是受虐癖和施虐者這段關係中的角色,她跳脫出來成為第三方,因此她的凌虐不再具有色情的意義。
成為第三方這一點也可由隨後的對白進行印證:托馬斯說“謝謝,女主人”,被旺達糾正為“謝謝,女神”。
此處的“女神”不再是受虐癖的理想形象“穿裘皮的維納斯”,而是酒神的女祭司(Baco/Menades)。
酒神女祭司指的是因崇拜酒神而拋棄家宅、回歸田野的女性們。
[9] 電影的結尾早在第32分鐘時由托馬斯講出:“實際上這是《酒神的女祭司們》的故事。
酒神狄奧尼索斯來到地球,讓底比斯的傲慢國王甘願男扮女裝去偷窺女祭司儀式。
然後那些瘋女人,酒神的女祭司們,把國王撕得粉碎。
狄奧尼索斯帶著勝利的榮耀回到家中。
”傲慢的導演托馬斯按耐不住心中渴望裝扮成旺達,認為自己真正懂得女性的慾望——被男人羞辱施虐,他自以為能夠窺探女性的內心世界。
但結果是被牢牢捆在菲勒斯之上,聽天由命地看著只披著一條裘皮的旺達用希臘語宣佈:“女祭司們,卡德摩斯[10],讓我們在酒神巴克斯[11]的音樂中舞蹈吧!
”此時的旺達終於在男性面前展開身體任其觀看(如圖四),緊接著一個旺達面部表情的特寫鏡頭,她的目光空洞不似活人,仿佛被神明附體。
男性在觀看裸體時得到的也不是快感,而是對獸性的驚懼(如圖五)。
接下來旺達伴著詭異而又激昂的旋律跳起了祭祀般的古老舞蹈,繞著托馬斯嘶吼如同要將他撕碎(如圖六)。
最後,勝利者帶著榮耀離去,以留下仍在驚恐中的、被拴在菲勒斯上無法掙脫的男性而告終(如圖七)。
酒神女祭司們放棄世俗生活,重新與自然建立親密關係,在行為中與野獸同化,哺育幼獸,互相殘食,從日常生活里逃逸,進入與神結合的瘋狂中去。
[12]這些行為被認為是瘋狂、野蠻、不可理喻的同時,也正說明了其與文明理性的對立,而後者正是父權社會的產物。
因此,電影結尾對酒神女祭司的戲仿傳達出了對菲勒斯中心主義下建立的視覺快感模式與精神分析的質疑與挑戰。
由維納斯到酒神女祭司的轉變象征著女性由男性主導下的被觀看的客體自發轉變為反抗壓迫、解放自我的主體。
在女性解放了自我,恢復了主體性自由離去時,男性仍然被他們擁有的菲勒斯所束縛得動彈不得,這或許暗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沒有菲勒斯並不必然導致處於從屬地位。
五、總結本文從受虐癖的角度切入,通過分析男女主角之間權力關係的兩次顛覆,來闡釋受虐癖的特質在情感關係中的表現,得知了權力實際上掌握在受虐癖托馬斯而不是施虐者旺達的手中、受虐癖通過支配施虐者來滿足自己的快感。
這種男性快感的獲取方式一方面來自對施虐者色情的凝視,從而滿足性本能的需要;另一方面來自對閹割焦慮的徹底否定,即通過將感情投入到一個物或是物化的人的身上,從而獲得安全感。
兩種方式結合而成的戀物的觀看癖幾乎貫穿整部影片。
然而如果分析兩個主人公在前半段電影里對中心表達所起的作用,或許正符合巴德·伯蒂徹(Budd Boctticher)所言:“重要的是女主人公所激發的東西,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她所代表的那些東西……她在男主人公心中激發的愛戀或是恐懼的感情,或者是他對她的關心、是她使他那樣做的。
而女性本身則絲毫不重要。
”[13]在菲勒斯中心主義之下,女性只是能夠滿足男性快感的客體。
但《穿裘皮的維納斯》沒有落入俗套,在男性快感獲得的過程中突然轉向,借酒神女祭司的神話,照應之前埋下的伏筆,對男性快感的表達反戈一擊。
酒神女祭司從日常秩序的出走和男性被綁在菲勒斯上的束縛,表現出對菲勒斯中心主義下男性快感的諷刺,兩者的對比也暗示了父權體系以外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整部影片的前後價值觀碰撞是本部影片的最大亮點,從主流電影角度出發再回到女性主義的反色情角度,豐富的內容使這部電影值得更多的關注與討論。
參考資料:Bogue, Ronald, Deleuze and Guattari. New York: Routledge, 2003.董學文,《西方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黃作,《不思之說:拉康主體理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勞拉·穆爾維著,周傳基譯,<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刊於《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年。
皮埃爾·韋邇南著,杜小真譯,《古希臘的神話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1]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New York: Routledge, 2003),46.[2]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New York: Routledge, 2003),47.[3].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New York: Routledge, 2003),47.[4] 勞拉·穆爾維(Laura Molvey)著,周傳基譯,<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刊於《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年),第564頁。
[5] 勞拉·穆爾維(Laura Molvey)著,周傳基譯,<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刊於《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年),第565頁。
[6] 黃作,《不思之說:拉康主體理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7] 勞拉·穆爾維(Laura Molvey)著,周傳基譯,<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刊於《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年),第571頁。
[8] 董學文,《西方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43頁。
[9] 皮埃爾·韋邇南(Jean-Pierre Vernant)著,杜小真譯,《古希臘的神話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86頁。
[10] 卡德摩斯,Cadmus,希臘神話人物,底比斯城的建立者,酒神的祖父,尊重古老的民間傳統。
[11] 巴克斯,Bacchus,酒神狄奧尼索斯的羅馬名。
[12] 皮埃爾·韋邇南(Jean-Pierre Vernant)著,杜小真譯,《古希臘的神話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86頁。
[13]勞拉·穆爾維(Laura Molvey)著,周傳基譯,<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刊於《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年),第568頁。
7 ) 酒神的笑声
BFI SOUTHBANK,STUDIO。
总共只有30几个座位的厅,屏幕却相当大。
四下一看,几乎没有女性观众。
第一排尽是鹤发中老年大叔,一水儿蹒跚着走进来。
我左边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老爷爷,身上带着一股略微刺鼻的,陈年老书柜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电影放映过程里他始终兴奋异常,偶尔拍案叫好,大多数时候频繁变换着坐姿;右边是两个奇装异服的文艺青年,挨着我的男生黑发披肩。
我知道这有些诡异,我有理由紧张,甚至害怕;但我仅有的精力都被这电影吸去了。
短短的96分钟里,除了几次会心的笑声以外,观众们始终是鸦雀无声。
就连移动姿势的声音也刺耳的惊人。
我知道不只是我,大家都被波兰斯基这出独幕剧牢牢吸引住了。
我身上的鸡皮疙瘩起来,下去,又起来,又下去,又起来。
电影有着完美呼应,眉飞色舞的开场和收尾。
两位演员,一个场景。
精彩绝伦,都说老婆该是艺术家的缪斯,Emmanuelle Seigner名副其实;可让人折服的是法国大明星Amalric,他要把自己置身于怎样的惊涛骇浪里,才能驾驭如此一波三折的角色;他们定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波兰斯基的理解延绵又坚决地缠绕不休,才能完成这样一出权力不断反转,又始终如一的游戏。
这么多年以后我又被一榔头打回到福柯,即使当时学的早已血肉模糊。
影片玩耍着博弈,玩耍着原作者马索克骨子里对权力的执念,玩耍着writer和adapter对人与人之间施与受关系的推挤,扩压,自我剖析;马索克的经历缠绕着他的作品,而波兰斯基对此的改编又附上了自身的反射。
难怪BFI的programme里写着Polanski's film is a version of a version of a version of a life。
回来豆瓣,发现大家都流畅地用自己的语言重现了影片的内容,我写不出来。
回忆起来,只见旺达取之不尽的手提包,舞台上冰冷的"仙人掌",“比喻意义上的咖啡”汩汩流下,“一年”契约上的“签名”沙沙作响。
和78分钟的[会客厅杀戮]一样,96分钟的[裘皮维纳斯]也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
我再次被无底洞一般的波兰斯基迷住了。
他是荧幕背后,同时自己也跳上屏幕的浮士德,以毫无退缩和懈怠之心邀约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幻影,女神——女主说她叫旺达,与试镜角色名一致,多么巧妙,又毛骨悚然!
——或魔鬼,随便取名什么。
如果把[会客厅杀戮]里桌上那瓶威士忌及其原作“杀戮之神”与本片最后的高潮酒神之舞相联系起来,又隐约可以听见狂欢的狄俄尼索斯放荡的笑声了。
8 ) 这个时代的共同trauma
在15年的时候慕名看过这部电影,看了一半便昏昏欲睡,只记得两个人仿佛在暗暗地争执。
在UCD上人类学的时候,教授的研究领域是SM和历史事件,诸如Slavery的联系,在课上提到了这部电影,于是翻出来重看。
教授曾提到的一些观点, 理论在影片中一一对应。
畅快淋漓地看完,大呼牛逼。
戏中戏不是一种很小众的拍摄方式,但这部片的的主题加上这样的拍摄方式实在精妙。
影片一开场,狼狈的女演员与挑剔的制片人相逢,两人的位置不言而喻。
然而女演员以台词与打光很快掌握了主动权,剧情开始变得跌宕起伏,两个人戏里戏外开始较量,戏中的旺达与男主角签订了奴役协议,戏外的旺达因那句性别歧视的“上帝惩罚他,把他交到一个女人手中”而与编剧发生争执。
是谁在操控谁?
剧中的旺达哭叫着“你让我奴役你,却是在控制我。
”剧外的旺达给编剧穿上了高跟,抹上红唇,披上象征恋物的裘皮扮演旺达。
剧中的旺达被捆在在象征男性阴茎的舞台道具上,剧外的旺达则披着兽皮,面目狰狞地跳起舞来,一如Dionysus的女祭司。
Dionysus,酒神,second-born god。
母亲因为想要一睹Zeus的真面目而化为灰烬,Hermes将他缝入Zeus的大腿,由母亲与父亲共同孕育的半神。
Dionysus象征着戏剧,酒与享乐,以及性别的错乱。
关于他最出名的故事,是在他回到故乡,被自己的表哥与姨母们所不承认,便使姨母与一些女人精神错乱,并教唆表哥,当时的国王,穿上女人的衣服去一探究竟,最后表哥被自己的母亲当成老虎徒手撕碎。
这个故事探究了性别模糊的可能性与其后果。
Aphrodite,掌管爱与美的女神,致使以Zeus为代表的新生代为数不多的混乱。
在这个男权的戏院里,Aphrodite的雕像被一个阴茎形状的雕像所代替,讽刺弗洛伊德将一切激情与冲动全都归结为对于阴茎的渴望。
在剧外旺达的建议下(这也是两人关系反转的开始),两人临时加了一场Aphrodite降临的戏码。
Aphrodite裸体躺在沙发上,身上抚媚地围绕着裘皮。
她因男主人公拒绝了了她而恼羞成怒,化成剧中的旺达而让男主人公发疯般地爱上。
在剧内Aphrodite的化身被捆在阴茎的雕像上,她在当代社会被阴茎论所代替,没人再记得她(这让我想起了,曾与Parker提到过Aphrodite,他说“Wow, I haven’t heard that name for quite a while.”)。
在戏外的旺达,导演处处暗示她正是Aphrodite的化身,质问这个男权的社会与趾高气昂的编剧。
她手持皮鞭,告诫我们不过都是她,欲望的奴仆。
电影里提到“不可知的一个瞬间”,在剧里是男主人公傲慢性感的姨妈,将男主放在裘皮上用白桦树枝抽打,从此他恋的便不是大腿,而是裘皮下的大腿。
教授在讲恋物时提到,当代的一些理论讲恋物,都追溯到童年时的某个时间,受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创伤(trauma)而对一些特定的物品或者被物品化的人类开始迷恋。
当剧中的旺达提问“小时候你的母亲用裘皮包裹你么?
“正是对这个瞬间的探究。
电影有无数个细节与无数个象征意义,裘皮在影片中不过是一张破烂的围巾,看不见的咖啡与欲望,现代的SM项圈与复古的衣着,旺达长长的皮靴。
这是一种变态么?
剧外的旺达与编剧争执不休,剧中的旺达是否是被迫的?
影片给我们的答案是:这是一种常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干草,有时只需要一个火星。
These are just the common trauma from modernness. --Donham
9 ) 140828
爱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因为简单,所以容易被附加很多东西。
在《爱的认识》当中,舍勒就陈列了从古至今西方人给爱赋予的意义。
在他们眼中,爱连结善,从而与有和完成展开联系,因为有,就有全,就有完整,于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有了全知全能全善的天主。
这一条思路下来,爱物爱人就同爱流溢中的天主展开联系。
这是很神。
在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再到之后,爱在认识论上的意义越来越强。
爱即理性,爱就是将物我距离去远的过程,这点海德格尔没有谈,如果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讲,几百年前的人已经不自觉的将认识和操劳操心画上等号。
这种爱,使没有关系的物我连在一起,从而在亲密无间中,我认识了你。
西方人看到的爱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显现在很久之前就有种子,古希腊人,与东方完全相反地,认为只有爱得深沉,才能获得更多意蕴,我了解的越多,你在我心中更完整,你更存在了。
这当然会影响到公用同一个字的爱情,爱的对立面就是没有爱的西方人,爱在自己的爱中,在爱中充斥自身的强力。
当他们看到虐恋的时候,他们惊讶,为什么有人这样放弃自己的尊严,尊严倒是其次,为什么这样放弃自己的存在。
在从很久之前就有自由因子的他们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人为什么要为另一个人,而不是天主,放弃自己。
当时他们没读过古印度的书,也没读过现代日本色情小说。
在他们看来,爱是过程,而非认识的结果,东方人放弃意欲而获得对方的充实而爱的逻辑是很陌生的。
所以不懂。
但在爱情中,性虐只是真真假假地放弃自己,没有感受到失去存在意义的人们只能体验那种痛的快感,从而在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而痛苦,在远离和常人占有欲之间挣扎的爱的边缘人,才是虐恋中最痛最爽的人。
在这几条路上徘徊的人们,也就是这个电影暧昧不清在描绘的。
10 ) 隐藏的伪娘和被抛弃的缪斯
从何说起呢?
如果不知从何下笔就从自己找到这部电影,并看下去的动力与目的吧!
算是我对美国或者模仿美国那种简单粗暴的电影的厌倦吧(其实我也几乎没有产生过兴趣)。
现在我真的愿意相信欧洲人瞧不上美国人是有道理的。
诚然美国人(早期的美国人,谁知道,反正都是我自己脑子里臆想的)曾经承认自己是粗俗的,也想着改变自己,让欧洲人看得上自己,可是他们失败了,当然有欧洲人的偏见这一原因,可是根本上的东西(连只是一点点复杂的天主教?
英国国教?
都搞不定的他们,能要求他们去擅长更复杂的东西吗?
),他们的确不行。
反正种种原因,他们失败了,当然美国人必然是聪明的,他们换了一条路,这是弱者的特权。
就是他们的聪明。
来证明他们的粗俗是合理的,伟大的甚至是普世的,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去反对他们曾经渴望被接受与认同的欧洲,欧洲之所以是欧洲的一切。
他们成功了,因为人数优势,人数何以成为优势,因为技术,因为普世。
举个例子,连哲学都成了一个技术活,那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最后技术胜利了,人民也胜利了。
这没有什么不好,换句话说,这多好!
可是那群被称为“做作,故作优雅高深”的东西,也要给它们一条活路,毕竟那些东西不是技术而是经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是思想不是智慧,是复杂不是简单。
难道我们应该以简单为荣,以复杂为耻?
你说这是堕落吗?
以上所写就当做是序言吧!
哀悼一下以复杂为荣的时代吧!
那是我们人类活在神话的时代吧?
也许。
说来电影,导演是罗曼·波兰斯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在强调他是大导演,别的大导演却没有人这样强调,这是梗吗?
原谅我的无知)。
本片值得玩味,各种意义上的“翻来覆去”,当然我要承认我梳理不来这些“翻来覆去”,所以我不能走这一条路,还是选择几个切入点,大概谈一下个人感受吧!
女主一直在反抗男主给予她的她应该有的一切,她认为这一切如此荒谬,怎么能这样想?
而男主即他却一直认为她就是如此,这才是她的本质,这才是男主体会到的她,而这是真正的她,伟大的她。
发现男性如此狡猾,“男主体会到的她,这是真正的她,伟大的她”,换一种说法,作为女性的她,如果意识到她的本质,她的伟大(当然这本质和伟大还是男性创造的概念,当然女性接受这个概念,是一种被强迫的行为,如电影中一般,女主虽然站在舞台中央,主导这舞台,可是依然被作为导演的按照控制,所谓,自愿臣服与她,不过是他强制她奴役他。
这是什么,一、完全的不负责,明明在行使权利,可是将这权利只是在形式上给予了女性,而义务和责任也就转移到了女性身上,男性丝毫不用负任何责任。
二、完全的软弱,不敢直面一切,需要创造工具来代替他的身体来直面世界,而女性正是男性接触世界的工具。
),对于男性来说,很好。
而如果没有意识到,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对于男性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他强加给她的本质和伟大首先说明他的本质和伟大(是他发现了这一切)。
其次最重要的一点,他其实就是他想象中有意义与伟大的她,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为男性缺少一项权利,即美的权利,或者说,男性不能是美的,进一步说,男性不能将美作为目的,我们不否认作为结果,男性肯定是可以为美的(当然我们还要排除那些本身就不想将美做为目的的男性,这才是正常的)。
但是渴望美,以美为目的的男性是有的的,至少艺术家中有这些男性(发现美,对于他们是幸还是不幸)。
所以他们意义化,神圣化他们心中的她,并且一步步的成为她,在心中,在纯粹中,他们成为了女性,在这里他们占领了女性的领地,终于将美占为己有,美终于可以正大光明作用目的被他所追求。
在追求的同时,并且隐藏了自己,谁也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认为高跟鞋是美的,是伟大的男性,其本质是渴望自己穿上,可是作为男性永远也不可能),以美为目的的男性,神化女性是他最高的自慰?
反正不论如何,女性从来都被男性放在一旁,看着男性玩着小孩子、“小女孩”、“妇人”等的游戏乐此不疲。
本片让我想起了《母亲》这部电影,詹妮弗·劳伦斯主演的那个。
其中作为母亲这隐喻的大表姐难道不就是被作家诱骗过来,并加以抛弃的缪斯吗?
一遍一遍的被进行加工,创造。
谁在乎,缪斯只是沦为了男作家追求美的工具。
毁灭,再重新来过就是了。
一切文字,旋律,影像,不都是如此,只要男性(这里的男性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男性,艺术作品的创造者,类似男性,现实意义上的女性会如此。
)能追求美就好了,其中他们歌颂的一切其实都不重要,不过是死了,再复活罢了。
谁关心受尽折磨的“母亲”,缪斯。
发现了个问题,电影之于我也不过如此,只是我阐发我思考的工具,我说电影越出色,越深沉也就越体现我的想法。
看来我就是一个伪娘,我要承认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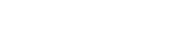











































2.5/5。挺不喜欢的一部,觉得没什么意思。
三星半,大变态,神头鬼脸,有一处转折不清,但确实对心理和戏剧的把玩到了炉火纯青
他又来了一次封闭空间啊!不过这次有舞台背景做工具,算作弊。看完这片我去把书找来读了一遍,发现十九世纪的色情小说就是当今的文艺作品,好有思想深度啊! 不管如何,只能说能把如此闷的情节拍成不太闷的电影,波兰斯基确实是个很会导演的人。
现实与虚假的交叉 支配与被支配的转换 两位演员火花十足 但觉得本片情节太过单一 几本就是“念台词” 这要是跟真正的戏剧比起来 就太小儿科了吧
★★★☆ 繼《Carnage》之後Roman Polanski又一部在有限演員和場景內完場的作品,而且也延續了前者的一些手法,揭露了道貌岸然面具下醜陋的面孔,只是相對前者,在主要角色再削去一半的情況下,為了支撐故事推進而將戲劇性更大化,人物關係反轉再反轉,甚至到結尾已經略顯失控。
有点无趣
反反复复打开了三五次又关了 反正我就是看不下去 身为罗曼波兰斯基的脑残粉 我还会再努力看的
美丽令人迷幻
又是封闭空间,人物竟比《杀戮》还少了一半。
求三流导演放过马佐赫。
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其实也是被台本鞭笞着牵着走,最终被绑在了巨大阳具仙人掌上的那个,脑袋被各种符号占领却还是为这出戏叫好,如维纳斯其实是在为所有有根者起舞。&lt;性瘾者&gt;那边还没了这边又响起了法兰西虐恋炮响,2014注定榨干
完全没有任何带入感
96分钟,前面90分钟可省略,看最后6分钟可以了,女主长的挺吓人
法版反情色
就是2个人的对话,闷啊,看不懂
过于理论和抽象,故事性太弱,结尾的转折毫无悬念。
罗曼·波兰斯基拉掉维纳斯的裘皮,撕掉观众的面具,在一次次猝不及防的优美反转中,让人体会权利支配的循环和变更,以及情欲的荒唐和堕落。电影在舞台与现实之间进行着奇幻的交织,这是由两个人书写的人性自白书,罗曼·波兰斯基的戏剧性已臻化境,它让人看着看着就傻眼了。
欧洲文艺白男只能当m,他们多希望跪下、凝视并亲吻黑丝皮衣高跟鞋刻板又性感的女王的脚。
影片最后女主说的话对那些等操的人来说是多么打脸。
封闭空间,二人对阵。施虐受虐戏中戏中戏,角色互换性别互换